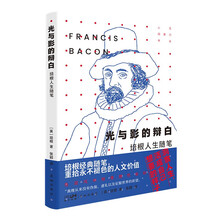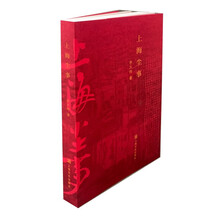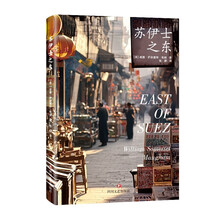在阿尔卑斯山脉绵延而下普罗旺斯地区一片无边的荒原上:他带了只口袋在大地上寻找完美的橡树、山毛榉、桦树……的种子,显然,他敏感的眼睛已和它们内部明亮的眼睛达成了一次交谈!几乎由不断弯腰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谦卑动作完成了“以一已之力拯救一片荒原,使之变成一片生机勃勃的乐土”的壮举的弧线——1947年安详地在班纳安养老院去世的牧羊人布菲耶,享年89岁。安详离世,大抵是因为在世时有着问心无愧的神圣的宗教情怀。旅行者吉奥诺说他是一位播种希望和欢乐的老人,用无私完成了一件神一样的伟业……
我做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梦,一个收集种子的梦……当阳光透过八楼的纱窗照在我脸上和这本浅绿色小书的封面时,我们仿佛看见了彼此脸上温暖的笑意。我已经整个冬天没有离开城市,看了一整个冬天毫无生机的偌大广场:枯黄的草坪,一株株不耐寒的铁树被稻草裹得严严实实,像极被高度灼伤的病人。这番景象常给我一种错觉:田野和稻草人。而这种错觉在数年前这里原本是耕地的时候,它就是真实的了。
稍前的一个时段,我曾愉悦地穿行在皖南大地上,那里秋收后的痕迹看起来那么崭新,我的眼前闪过雪亮镰刀飞舞的轻快节奏。农家生活简单的曲线,缓缓升起的温暖炊烟,家禽绅士般在悠闲地散步,隔着车窗玻璃我分明还能闻到粮食的香甜气味。在广阔的田野中间,竖着一块高大的牌子,虽然这巨大的金属破坏了一片田野的美,但我乐意接受它书面书写里凝聚的力量:保护耕地,我们别无选择。这十个普通的方块字紧挨在一起,有着誓死不离的坚定,以一种经过沉思后的罗列秩序,暗涌着惊心动魄的呐喊。
慵懒不妨说是一种臃肿的懒,它让我失去了之前生活必要的营养补充:下弦月、启明星、田野、树林、落日,我一天可以相互亲近的部分。我把这些替换成一些盆栽的植物,遍布在屋子的角落,如此我才能感受活着的气息。整个冬天,我的餐桌摆放着不同种类的水果,我很少吃它们,等它们变色了、干瘪了,我又重新买回一些替换它们。这是我一个人的版图,比如嫩黄的香梨,它来自新疆库尔勒;比如橙红的脐橙,它来自赣南……我喜欢这些颜色并想象着它们故乡的繁茂,每天看看它们,我的内心生活仿佛还曾富有。我还喜欢买回各种蜂蜜,紫云英、槐花、椴树……我分别不出味道的好坏,这些味道被鲜美的甜淹没掉了,所以我不是一个适合品尝蜂蜜的人,我只是想象我是一个放蜂人,正带着我的蜜蜂去备个地方看各种美丽的花朵。
偶然向窗外探一下头,才惊觉楼下一小块裸露的泥土上,菜花开了。一个妇人正站在那里,她挽一个小篮子,时不时弯腰,从泥土里寻找她需要的东西:荠菜。已经是春天!整个冬天我都没有发觉自己是多么的迟钝。手头捧着蕾切尔·卡逊的书《寂静的春天》,时光流经了她当初的预言年代,逐渐应验为事实。我的想法很多,此刻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去收集各种备样的种子,只要春天准时来临,我就能拥有自己的花草,那些在荒芜边徘徊的人是多么羡慕我这个富翁。
我的眼睛就像在爬楼梯般阅读着这座城市,密密麻麻的房子一幢高过一幢。原本一座村庄里,最高的是树,现在它们最矮了。它们彼此都不认识,像我一样,一个没有邻居的人,从各个地方搬迁过来,过着不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这段日子我一直在寻找一只鸟,这段日子我也一直感激这只鸟。在我整理书稿《庭院》的二十余天里,也就是大致从春分之后的几天起一直到谷雨这天,这只鸟非常奇怪又准时地在凌晨三点四十分左右开始了她的独唱。她的声音清脆,婉转,多节拍,在我所听见的鸟类的声音里完全是个异类,我总在猜想这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在异常嘈杂的城市里如此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她基本上坚持着独唱到四点二十五分左右的习惯,然后在群鸟纷纷歌唱时悄然隐退。每天,我轻轻打开窗户,循着声音的方向试图寻找到她,可以确定,她就在离我不到100米的地方,也许她看到了我的眼睛并从我的眼睛里猜测到了我的想法,她嫣然一笑继续歌唱。而我,再轻轻关上窗户,像她练习歌唱般继续抚摸时而宁静时而汹涌的文字。我们都已明白,这座城市彼此都不曾孤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