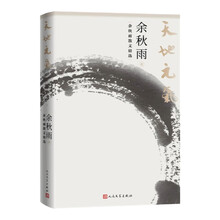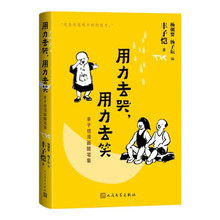大尾巴狼的一天
天不亮,在各种闹钟(包括左邻右舍装修的电钻)的轮番催促下,他努力睁开惺忪的睡眼,穿过一个又一个工地,一个又一个停车场,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到城市的另一端——他所在的那个“工地”上工。天黑了,还是沿着原路,蓬头垢面的他缓慢而蹒跚地摸回他的“工棚”休息,一路上还担心着今天究竟是会停水还是停电。夜里,除了工地的尘烟和灯火,看不到星星和月亮,他苦苦地抵抗着内心的噪声,在不得不睡时靠安眠药睡去,焦灼中等待着新一天的电钻声。
这就是他的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朝九晚五中奢望朝三暮四。有人嘲笑他是大尾巴狼(尾在这里读yi)——每餐有肉,出门有衣,隔三差五还能混顿小酒,看场大片,这日子已经够不错的了,居然还他娘的有这么多感慨邪念,纯是转基因色拉油蒙心,吃饱了撑的。
这话不无道理,但他却深以大尾巴狼的称号为荣。大尾巴狼总比大尾巴狗、大尾巴猴、大尾巴羊、大尾巴鸡要强!大尾巴鸡?那应该叫孔雀,也就是那种常见的顾毛不顾腚的鸟。
其实,大尾巴狼的生活也没什么优越感可值得炫耀。所有“工地”上工与下工的哨声总是整齐而准点,雷打不动。每一天他消耗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呆在“工棚”的时间却越来越短。除了“工地”上的一顿午餐盒饭,其余在家的两餐按时间来说都应该算夜宵,而唯一的娱乐就只有看那些电视台颠过来倒过去胡乱播放的电视剧了。电视成了他每一天唯一的寄托。某一天,邻居家失窃了,据说是在大白天,小偷悠闲地带着搬家公司和开锁公司轻松便完成了全部工作——连厕所的手纸、新买的大米,外加天花板上的灯泡都没放过。当这位邻居下工后匆匆赶回来,面对着空空如也的家放声大哭:“都没了,连彩电都搬走了!”是啊,饭可以不吃,厕所可以不上,但没了电视,这一夜可怎么过,彩电失窃是邻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看着自家还在的电视,大尾巴狼深感后怕。回家成了一件让人盼望又让人害怕的事情,于是路上大尾巴狼便会对那些悠哉的“城市边缘人”心生羡慕。人家可以自由来去、乞讨、收工,人家可以边抱着孩子边做小买卖,或推着自行车左顾右盼惬意地等待大买卖。人家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天气不好还可以在家窝工,不考上岗证,甚至连卡都不用打。相比这些人的日子,大尾巴狼的生活则忙多了,忙里偷闲在路边喝口凉水都可能塞牙。一天,在冷饮摊他买了杯饮料,杯上印着一条谜语:小小珍珠真可爱,不能玩也不能戴,小朋友们想去摘,手碰珍珠就弄坏(猜一自然物,谜底请见下一杯)。看了半天大尾巴狼深为不解,水没顾得上喝一口他便忙问售货员:“见下一杯是什么意思?”售货员颇不耐烦:“再买一杯不就知道了嘛,还在乎这点钱!”
大尾巴狼的另一个爱好就是每天夜里在小区贴标语。新建的小区,广告上的绿地人间蒸发,内外墙皮掉得稀里哗啦,房屋面积缩水,卧室时常漏水,厨房龙头经常没水,厕所地漏不通下水……真是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张贴标语来曝自家隐私慢慢成了一种习惯,好在天一亮夜里贴的标语便会准时不翼而飞,所以贴标语成了大尾巴狼永不下岗的一项工作。
夜深了,在大尾巴狼的梦中,偌大的城市像是一只开始蜕皮重生的巨型冷血动物,周遭一片喧闹,他努力置身其中,仿佛似一粒尘土,等待掘土机掘起,等待压路机压过……大尾巴狼每一天都在这同一个梦中惊醒(不用问闹钟又响了)。之后起床,左手拿上皮鞭——督促自己,右手举根胡萝卜——给自己以希望,之后向着“工地”进发,开始新的一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