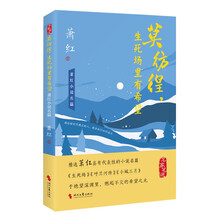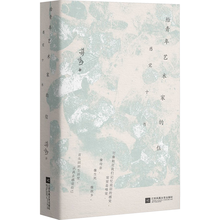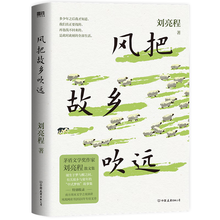我有好长一段时间轻视莫扎特,大概和看过那部《莫扎特》的电影有关,那部影片没让我对莫扎特留下什么好印象。在影片中,莫扎特似乎总是疯疯癫癫的,老是打情骂俏,老是让人人嫉妒算计。
我对二百多年前的莫扎特一无所知。
我开始对莫扎特有好感,是读了巴乌斯托夫斯基写的《盲厨师》一文之后。那篇文章写得很美,三十多年前,我曾经将它全文抄过一遍,抄它时的那个春雨霏霏的夜晚,至今记忆犹新。夜雨扑窗,悄然无声,仿佛是莫扎特从遥远的地方走来,走到我的面前。是它让我走近莫扎特,让我为自己的无知和浅薄而脸红。
文章写的是一七八六年维也纳近郊风雪呼啸的一个夜晚。给一位伯爵夫人做了一辈子厨师的盲老人,在他的破旧木屋里奄奄一息孤零零地就要去世了。在忏悔了一生所犯的过错之后,他唯一的愿望是能够重新看到早已经故去的他年轻时的恋人,依然出现在早春苹果花盛开的树下,向他款款走来。可是当他说完这话,就嘲笑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是自己的病把自己搞糊涂了。怎么可能让一个盲人重新看见人,而且是看见岁月倒流早已逝去的年轻时光和年轻的恋人呢?顶着风雪,走进他这间小木屋的一个年轻人,却对他一连大声说了三遍我可帮你做到!在盲厨师小木屋里那架落满灰尘的破钢琴旁,年轻人坐下,为老人弹奏了一支即兴曲。他弹奏的这支曲子太神奇了,在乐曲中,老人竟真的看见了自己年轻的恋人,走在了早春苹果花盛开的树下,老人打开窗子,扑窗而来的大片大片的雪花,真的觉得就是那芬芳的苹果花。就在美妙的一瞬间,老人幸福地合上了眼睛。
这个年轻人就是莫扎特。那一年莫扎特整整三十岁。
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莫扎特和他的音乐都是那样神奇。美好的音乐,能够抚慰人哪怕创伤再深的灵魂,能够创造人无限向往却无法创造的奇迹。我想起歌德曾经对莫扎特的高度评价:“像莫扎特那样一种现象,实在是无法解释的奇迹。”
很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这个故事之中,我不知道莫扎特为那个盲厨师弹奏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钢琴曲,却仿佛听到了那美妙的乐曲,心久久地在那乐曲中荡漾。我为莫扎特,也为那个盲厨师而感动。他真是个幸运的人,虽然他的一辈子吃过那样多的苦楚。但有了临终前莫扎特的那一支钢琴曲,他值得了,所有的一切辛酸都融入了音乐之中,化为了永恒的旋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他这样的福分。
莫扎特实在是伟大的,是他才让那纷飞的雪花变成了早春盛开的苹果花的。
怎么可以轻视莫扎特呢?
当然,我们必须拥有盲厨师那样对年轻时恋人和苹果花的渴望,对音乐和生活的虔诚,才能够感受到那一种境界:纷飞的雪花迎面扑来,才有可能化为温馨的苹果花。如果我们梦想着纷飞的雪花飘来最好是大把大把的钱票子,我们临终前渴望的不是心中珍存的那一份感情,而是如何立下分赃的遗嘱……怎么可以如盲厨师一样感受出音乐给予他独特而美好难再的境界?莫扎特便离我们遥不可及,远在二百多年以后,我们便很难在音乐厅在街头,更难在家中在心中,和他相逢。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各种非理性的情欲,都可以在音乐中得到净化。”那是指听众是如盲厨师那样敢于忏悔自己一生过错的人,敢于承认自己心底欲望的人,方才可以让各种欲望在音乐中得到净化。我们泛滥着太多拥有高级音响、懂得音响、收藏唱盘、占有音乐家如同占有庄园和情人一样富有的发烧友,而缺少盲厨师一样的贫寒却真诚的音乐听众,我们当然很难和莫扎特相逢。
我们当然会轻视乃至漠视莫扎特。我们会如数家珍将许多流星般流行歌星的名字口水一样挂在嘴边,而遗忘甚至根本不知道莫扎特是谁。指着莫扎特的照片和画像,我们只能说是个外国人。
德伏夏克在布拉格音乐学院执教的时候,不允许他的学生轻视莫扎特。他曾经在他的课堂上提问一个学生:莫扎特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学生回答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这样的回答,我想现在我们很多人会如此所答非所问,司空见惯不会脸红而只会无动于衷。当时,德伏夏克非常恼火,抓住这个学生的手,把他拉到窗子旁边,指着窗外的天空厉声问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学生莫名其妙,异常尴尬。德伏夏克气愤异常地诘问他:“你没有看见那太阳吗?”然后严肃地对全班学生讲:“请记住,莫扎特就是我们的太阳!”
我们是否听得到德伏夏克这严肃而响亮的声音?
莫扎特是否能够成为我们的太阳?
我们会有时间抬起头来望一望我们头顶的太空还有没有太阳吗?P7-9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