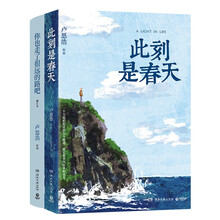上得楼来,只见一屋子慌慌乱乱的人。平素不常走动的伯母、婶母、姑妈等等亲戚都来了,团团围着躺在床上无声咽泣的母亲,劝慰的,垂泪的,乱成一锅粥。<br> 我才知道,父亲在菲律宾去世了。<br> 消息是由在马尼拉的大伯父传回来的。父亲在远离马尼拉的纳卯埠一一听说是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屿城市——帮族亲开设的一家商店做事,半年多前发现了这个不治之症。他最后的一段日子是在自己大哥的身边度过的。他的后事,也由伯父一手料理清楚,然后才写信传回唐山家里。<br> 母亲见我到家后挣扎着从床上支起身子,一把将我搂进怀里。至今,她那泪湿的、凄然的声音,还不时在我耳边响起:——孩子,你没有爸爸了!爸爸?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是个模糊且遥远的影子。……坐在高高的门槛上,两个稚齿蒙童不知为一件什么小事争了起来。拿着一块白白软软橡皮擦的那个,把手举得高高,炫耀地说:“我爸爸是开大商店的,有很多很多橡皮擦,你没有……”<br> “我爸爸……我爸爸……”我不知道爸爸是干什么的,猛一急,突然蹦出一句:“我爸爸是开橡胶园的,橡皮擦比你更多更多更多……”<br> 这话不知怎么被人听去了,学给妈妈听。当夜,妈妈搂着我,我感到眼泪滴在脸颊上,痒痒的。<br> 那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日子。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断绝了。妈妈靠她一双手,白天替人家洗衣服,晚上熬着黯淡的灯光织毛衣(妈妈织得一手好毛衣,会打百十种花样),艰难地拖带着我和弟弟。只有偶然在深夜里,突然响起一阵急急的敲门声,伴着低低的叫唤妈妈名字的声音。<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