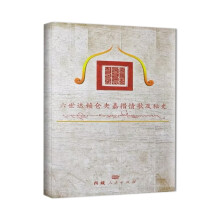十六岁,青涩稚嫩的年纪,喜欢雷逸臣的声音,每次听他的节目我都会变得安静,他的声音如此温柔,略微沙哑。
在整整三年中,听他的节目是我唯一娱乐,甚至高考前一天还在听。
A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我买了随身听,一个人静静地守候雷逸臣的声音,我给他写信,一封又一封,他念过其中两封,当他念我名字时,我欢喜得抚住了脸。
想去见一见雷逸臣,好几次站在电台门口,看着银色栏杆里那幢红砖楼房便心生怯意。我不知如何告诉他,多年来是他陪伴我寂寞岁月,他定然将我视作一个忠实听众,如此而已。
我希望自己足够好,出现在他面前不会自惭形秽,手足无措,可以淡定从容。我用功读书,急切地想要蜕变成配得上雷逸臣的女子。
某一天,雷逸臣的节日忽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体育新闻,全球各地的体育赛事,谁夺了冠,谁败走麦城,谁与谁一决高下。
我打电话去电台打听雷逸臣的下落,一个中年女人回复我说,雷逸臣辞职了。
请问他去了哪里?
不知道。
雷逸臣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彻底的,干干净净。我不甘心,接连几天都去打听雷逸臣的下落,一直是那个中年女人接电话,后来她记住了我的声音,索性硬生生地说没这个人。
我丢掉了雷逸臣,努力来到A城,以为近在咫尺,却骤然成了路人,再也没有他的声音,那个熟悉的时段,我一个人坐在秋千上晃来晃去,抬头看满天星光,轻轻唱着《海上花》。
记忆就停在了那年那月,永远不会衰老。
我拿到了奖学金,请客吃火锅,A城虽然地处江南,但冬天,那种深入骨髓的阴冷照样把人吹得极单薄。一行六人逃也似地钻进店内,闹哄哄地点了许多菜,还有啤酒,我再三推辞,还是被她们灌下了两大杯。
酒精在胃里翻腾,我跑去洗手间,对着抽水马桶剧烈呕吐,然后有人轻拍我的背,是一个男人,穿着黑色风衣,面容清秀。
我一脸惊愕,他拉过厕纸,微微俯身,替我擦拭嘴边的污迹,笑着说,你走错厕所了。在我尚未回过神之际,他已离开。
又一个男人进来,看到我,立刻后退两步,核对门上的标识,我急忙低下头,缩手缩脚地跑出去。
坐下来,左顾右盼,想要再看一眼那个黑衣男人,一无所获,我抚摸嘴角,回想他的温柔举止。
雷逸臣永远不会知道,因为他,我才会变成一个好学生,在师长们的惊讶里考上了A大,并且保持着优秀。他也不会知道,有一个女孩曾经如此眷恋他的声音。
雷逸臣,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标本,是一种声音,吸引着我来到A城,我想事实就是这样吧,日子如流水,雷逸臣渐行渐远渐无声。
三个月后,我又遇到了那个男人,在~个小型的摄影展上。
他穿着淡色毛衣,蓝色牛仔裤,身边是一个年轻女子,他们迎面走来,我立刻认出了他,目不转睛地紧盯着,他侧身和身边的女子说话,与我擦肩而过。
我百无聊赖地继续闲逛,一路将那些形形色色的照片看过去,他对我毫无印象,使我有一些懊恼。
同年秋天,在星海游泳馆门前,我和他第三次遇见,他开着辆黑色的摩托车,没有戴头盔,从我身边像一阵风般掠过。
在一九九八年,我们邂逅了三次,后两次是我见到了他,他却没有知觉,我不知道是否也有他见到我、我却浑然不知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我给一个初中生做家教,那个小女孩很用功,但成绩始终不够出色,她总是用一种痛苦的眼神看着我,我不是她的神,只能尽量耐心地解答她的迷惑,除此以外,都需要她自己慢慢摸索。
我也曾与她一样,对着满桌的书本心怀恐惧,对着空白的试卷无从下手,那么深的夜,小镇的人都已睡去,我一个人在灯光下,对着一道道题,开了一道道门,直到七月,豁然开朗。
每个周六午后,我都穿过半个城市去小女孩的家。一直希望自己坐在公车上,是为了去看喜欢的人,给他做饭,洗衣,看场电影。
但我始终找不到心仪的人,看着别的女生挽着男友的胳膊作幸福状,就默默地对自己说,宁缺毋滥,宁缺毋滥。
一九九九年的平安安舞会,我没有舞伴,看着别人双双对对地翩翩起舞,凄惶,就这么翻天覆地。明了寂寞的滋味,明了笙歌正浓时自己陡生的寒意,明了这么好的青春,无人分享的孤单。
一九九九年,我还是那个衣着朴素笑容恬淡的女子,各种奖学金似乎为我度身订做。我又一次拿到系里新设的某个奖学金,破天荒没有请客,她们眼巴巴地等着,我淡淡地说,我要去买衣服。
她们集体失望,没有人愿意陪我去逛商场,于是独自跳上一辆的士,叫他开到虹桥友谊商场,A城最好的女性服饰专卖店。
我在高雅宁静的商场里从容挑选,看到昂贵的价格还是不慌不忙地试穿,然后挑出些莫须有的瑕疵,遗憾放下。在梦一样的霓裳里,我挑中了一件黑色长裙,对着镜子,有片刻的晕眩。我从来没有这样美丽过,也不知自己有如此精致的身段。小心地问营业员是否可以打折,她抱歉地摇头,我舍不得脱下,还是咬牙买下了。
这样一件美艳至嚣张的衣服,在校园里没有用武之地,一九九九年最后一个夜晚,她们都和男友结伴去A城各种喜庆的地方,度过经典一瞬。
我一个人穿上黑色长裙,松开辫子,拎着裙子在繁华的夜街漫步。后来,我去了来来迪厅,我不能让自己的世纪末没有一丝意义,我要去一个有快乐的地方。
票价很惊人,我第一次去这般昂贵至疯狂的地方,一走进去,就丢掉了自己。音乐撞在铜质的地板上轰轰作响,四周灰暗,灯光如烟花乍起,把眼睛刺激得睁不开。爆米花的香味弥漫于整个空间,舞池里站满疯狂扭动的人,他们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真的是世纪末了,连快乐都透支。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有人贴着我的耳朵,喂,一起来。
他熟稔地拉过我的手,挤到舞池中央,虽然很少蹦迪,可身处那样热烈的气氛里,我很快融入进去,觉得身体轻盈且有悟性,他在对面跳各种姿势,我扫一眼便会了,后来我们对跳摇头舞,我的长发乱得没有章法,已经很累了,但身体失了控,还在左晃右摆,旋转,颠倒,天昏地暗。
十二点钟声响起,舞池上方悬挂着的七彩灯里纷纷落下许多小礼物,他那么高大,一抬手,就抓住了一只碧绿的小怪物,手里捧着大红色的心,脸上有痴迷的笑容,他放到了我手里。
目光交织,周围的喧哗一波波涌来,心里拥挤一片。
我的世纪末,穿着美丽妖娆的黑裙,在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个夜晚,邂逅了他。
快散场时,他与一帮朋友道了别,送我返校,走在冰凉的石子路上,他问我,怎么会一个人去来来呢?
我不想让他识穿我的寂寞,于是撒谎说,与同学走散了。
我们交换了名字,梁亦农,徐缇兰。
我侧身从铁栏杆的缝隙里钻进去,他笑着说,这么娴熟,是不是经常晚归?
这是第一次,我也笑,但白天踩过点。
一个人提着裙子在校园里走,恍惚间想起,已是另一个世纪了。
与梁亦农的交往惊人得顺利,他那样英俊慷慨,总是带我去罗蔓喝咖啡,去西西里吃牛排,耐心而温柔地示范拿刀叉的姿势,就像那天晚上跳舞一样。
他给了我一只小巧玲珑的手机,每隔十天半月都会悄无声息地缴了费。我不知道运气怎么一下子来了,过往的郁郁不欢一扫而空,我始信灰姑娘的童话。
我像她们那样循序渐进地展开了恋爱,从牵手到拥抱,到接吻,到抚摸,到肌肤相亲。像她们那样经常晚归,偶尔不归,像她们那样初谙了风月,变成另一个女子。
二〇〇〇年春天,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梦一样。
其实,与梁亦农在一起,更多的是填补寂寞,满足虚荣,至于爱不爱他,似乎从来不是一个毖须面对的问题。
毕业前一个月,我在一家外企顺利找到了工作,梁亦农为了替我庆祝,在家里开了一个PARTY,虽然以我的名义,可我还得替那帮打麻将的端茶送水,真狠,一下子开了两桌。
最后一杯碧螺春给一个男子,他抬头看我,谢谢,就放桌上好了。
咣当一声,杯子跌落,滚烫的液体迅速地蔓延开来,白色桌布的一角急剧变灰,他躲避不及,裤子也湿了一片。
梁亦农走过来,叫另一个女人收拾残局,我头重脚轻地往卧室里走,扑倒在床上。
记忆像嗅觉灵敏的猎犬,顺着气息摸索着前行,还记得那些年少的日子,犹如朝圣般虔诚纯真。
梁亦农推门进来问我,怎么了,缇兰?
没怎么,我干巴巴地说。
梁亦农抚摸我的头发,休息一会,不用招呼他们。
后来,我还是出去了,坐在沙发上看他的背影,听他说话,他欣喜,无奈,懊恼,失落,说着东风,白板,碰。
眼见他们快散场时,我谎称回学校,躲在楼下暗处,我要跟踪他,不能再一次让他消失于茫茫人海。
后来他上了一辆的士,我立刻伸手招了一辆紧随其后,方向朝西,开往偏远的郊外,内心执著的意念使我毫无怯意。
虽然同在A城,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一带,他进了一幢旧式楼房,我去敲他的门,过了很久,门拉开一条缝隙。
你好,我朝他笑了笑。
他记得我,放我进去了,径自躺回床上。
房子是一室一厅,地板上堆满了画报,酒瓶,衣服,家具只有电视机,洗衣机,和一台单门冰箱。
他略微坐起些,点了支烟,打量我。
我坐在唯一的椅子上,有些局促不安。
你找我有事?
没有,哦,有的,他一开口,我就慌乱了。
请说,他朝地下掸了掸烟灰。
我喜欢你的声音。
我快要哭出来,起身走过去,安安静静地伏在他胸前。
如在云端。坐着公交车去城西看他,给他做饭,洗衣,一起去看场电影,或者逛夜街,吃滇南米线,烤羊肉串。
他搂紧我,是我找上他。他拥抱我,是我抵不了他的诱惑。他亲吻我,是我靠近他。
和梁亦农谈分手时,他非常惊讶,他认定我会像别的女人那样死缠他,分手应该由他果断提出,而女人则哀哀戚戚地离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