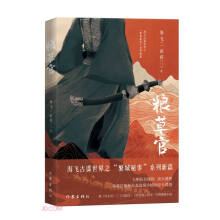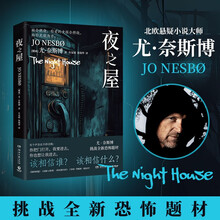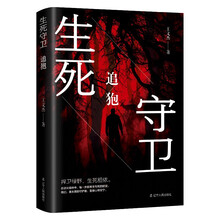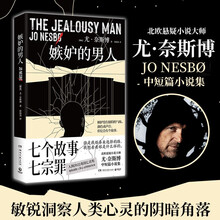气是近不了身的,所以有它在就不用怕。但一定要在阳烛点完之前过了原本建墙的地方,不然就惨了。”唐诗说起来语气淡淡的,那句“不然就惨了”也完全没有真实紧张感,他见我们不应答,又问:“明白吗?”
我和周长笙互看了一眼才慎重地点了点头。
分派下来,我是六楼,从主楼西侧往次楼东侧的墙引。
唐诗是五楼,从次楼东侧往主楼西侧的墙引。
周长笙则是四楼,跟我一样从主楼西侧往次楼东侧的墙引。
三人一散,我就点着红烛到了六楼的楼道尽头,烛火的照明范围根本不大,总觉着会从哪个看不见的角落冒出来些什么,说一点不怕那铁定是骗人的。回头去看五楼的西侧,隐隐约约看见一豆大的烛火摇曳,确认那边的人是唐诗,而周长笙则是在四楼跟我同样的走道位置。
这么想着,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像是野兽一般粗重的呼吸声,仿佛还感觉到那般气息灼喷在脸上,带着腥臭的味道。我那一刻是惊得心口腾地发痛,差点两脚发软就倒下去。
我把蜡烛捏得死紧,壮着胆回头去看,那一楼道上满满地匍匐着腐烂焦黑的人体,从地面墙壁一直绵延到顶檐,那渗着出来的水全部都是浓黄的,那么一眼我顿时觉得力气都被抽空了,想要拔腿就跑,但就死死地钉在那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