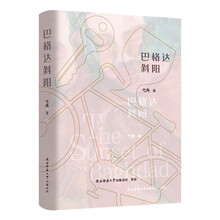民国初年,官方将祠中享堂、官厅、斋舍等都改成了教室,在此创办县立第二高小,成了我们这一带很好的学校。地方上有能力送孩子上学读书的,都会把孩子送到杜子庙去读书,其荣耀感不亚于如今上北大、清华。<br> 我母亲在杜子庙没有念完小学就出嫁了。很快中国解放了,我母亲作为一个开过眼睛读过书的有点知识的妇女,被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所感染,求知、求上进的欲望非常旺盛,在肚子里怀上了我的那一年,决心要去杜子庙念完高小。她挺着大肚子,带一点米,在路边捡一点柴火,在杜子庙某一个青砖墙的角落里,架上两块草砖,煮一点饭勉强塞饱肚子,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完成着学业。有一天大雪,我舅舅搀着我母亲放学回离杜子庙更近的外婆家。我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她挺着大肚子像个皮球一样在雪原上滚去好远,吓得我舅舅大哭起来。我在母亲肚子里顽强地硬撑着,毫发无损,支持着我母亲拿到了杜子庙的高小毕业文凭。我母亲凭着这张含金量很高的毕业证和在杜子庙练出来的一手好毛笔字,把我生下来还没有坐完月子,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要有知识的人才,我母亲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妇女干部,后来做了小学教师。<br> 从情感和距离的角度来说,我们家与杜子庙都是很近的。<br> 在我出生四十多年后某个阴雨纷飞的春日,有三十多个日本汉学家专程来平江拜谒杜甫。他们此行来访中国的目的,一是要到河南巩县去拜祭诗圣杜甫的出生地,二是要到平江来凭吊杜甫的亡故之处。他们的第一个目的没有实现,因巩县地方还来不及整修杜甫故居,觉得对不起外国友人,便找了些理由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拜谒。这批杜甫的崇拜者便按中国人敬奉先人的方法,买了一应香烛祭品,在郑州郊区找了一个能烧香的地方,朝着杜甫的出生地,跪拜敬祭了一番,以表一番仰慕之情。<br> 为了第二个目标不至扑空,到平江来拜杜甫墓时,日本人多了个心眼,没有和地方相关部门联系,也不打算请导游。他们在长沙租了两台面包车,一路问到了离县城二十余里,当年杜甫落葬的安定镇小田地方。那时候到杜子庙还没有通公路,只有一条仅供拖拉机通行的机耕路可走。老天只下了半天雨,路面便成了一汪泥浆,这面包车秀气的轮子一碾上去,整个车身当即便黄了一半。在日本人虔诚而固执的要求下,少见乡村世面的长沙司机一步三滑、东歪西侧地将车子开上了机耕路。走出两三里,因山体滑坡,一根倒伏的电线杆子,把路给堵死了。村中公路没有养路工,天气恶劣又找不到人来帮忙。眼见得快要到目的地而又不能实现目的,日本人甚是沮丧。一打听还有七八里地,大家打算弃车走路过去,但车上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看来冒雨蹬泥不是一件易事。<br> 这时有农人路过,见有贵客万里迢迢来访杜甫墓,便说还有另外的机耕路可绕行,并主动表示愿意带路前行。东洋人顿时雀跃,不断朝这好心人鞠着躬。在当地人的引导下,面包车抖抖索索绕行了十几里路,终于来到了日本人渴慕已久的杜子庙。但此时的杜子庙,已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响彻着朗朗读书声的百年乡村学府,已不能再让学生坐进去了,说不定一阵风吹过,就可刮倒她孱弱的身子。当地政府有意在老学府旁边修了个新学饺,希望我们的后代能够多沾得一些老杜的灵气。<br> 从日本人的兴奋状态上,看不出丝毫嫌弃杜子庙破败的迹象来。当他们踏进这光绪九年(1883)重修的庙堂和墓地时,还绽开了深爱着老杜才华的国际级学者才会有的笑意和欣慰。也许这些出自光绪九年(1883)以前的砖瓦、木料和建筑的风格,更能够让日本人钦慕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和民族。<br> 无人管理的庙堂里,雨水往内面灌注下几寸深的泥浆,当日本学者们欣喜若狂地冲进昏暗的庙堂时,很快便发出阵阵尖叫,大部分拔出来的脚,都把鞋子留在了此地特有的黏土泥浆里。尽管这样,并没有影响学者们收获的喜悦。他们在光绪九年平江的有识之士重造的墓碑及众多记载中,读到了他们不到实地考察便读不到的东西。走时他们纷纷捐款,他们多么希望这个有着极高文化学术价值的祠庙不至破败和消失。<br>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平江人开始修缮杜子庙。也许用勒紧裤带和牙齿缝里省钱米的形容词不大准确,但在这个有钱修宾馆修歌舞厅的时代,要筹钱来修这产生不了经济效益的祠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毕竟时代不同了,人们也意识到了一个杜甫的名声,可能就是经济效益和地方形象。这样杜子庙不久也就有了新的容貌。待那些日本学者再来时,想看泻泥巴也看不到了,再娇气的汽车也可以一尘不染地停靠在昔日杜子庙前宽大的场坪里。<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