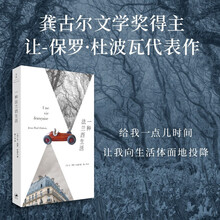外省书<br> 卷一 史珂<br> 一<br> 史珂一踏上这条小路就有点后悔。前边是那座孤零零的大屋子,它压在一片杂树林子里,黑乌乌沉甸甸。他像被它的磁力抓住了似的,每一次都要迎着走过去。屋里有个行动不便的人半坐半卧在大炕上,旁边站着他的外甥女。炕上的人每扫来一眼都令史珂不悦,他开始坐立不安。他心里说:我这回是来告别的……杂乱空旷的大屋子简直汇集了全世界的隐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四周弥漫。再到哪儿去呢?他徘徊,踌躇,磨蹭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坐到了炕边那把破藤椅上。他接过姑娘递来的一杯老茶吸吮着,开始怜悯自己。他知道炕上那个高高大大的家伙已经足他的朋友了,他们大概无法分开。<br> 秋天刚刚来临,这个额头鼓鼓的四川籍小女子就采来了菊竽花。她何等尽职,这会儿已经在屋角生起了废油桶改制的大火炉,烧好了洗澡水。屋角挂了浴帘,遮住了当地出产的一个粗陋的大浴缸。每天一早,热气腾腾的浴缸里总是浸了苦艾、桂叶、拳参、冬青一类草药,她给他搓洗,呵斥,直忙到九点多钟。史珂每次进门都要迎着满屋刺鼻的草药味,透过水汽看那家伙歪在炕上读书。满头披挂水珠的外甥女笑吟吟的,一见他放下书就走过来,听着他对来客数数叨叨。<br> “你看看这孩子的头发,我的老天!密匝匝苘麻一样,一把都攥不透。她的小嘴儿一天到晚湿漉漉的。鼻子翘翘着,脑瓜四周全是小绒毛儿……我这辈子也没见这样的小脑瓜。老天,胸脯上趴了两只小鹌鹑,一天到晚沙啦沙啦叫……”<br> 史珂额上的血管突突跳。他砰一声搁了杯子。<br> “我不说了,再不说了——这总行了吧?哎哟我的老伙计……”<br> 姑娘到浴帘后面去了,大概是放掉洗澡水,传来哗哗的水声。她再次回到炕边照料病人:“你呀,你呀!”她推搡他,把毛巾围上他的下巴。史珂低头吮茶,像打瞌睡一样。他心里又在琢磨:自己真不该再到这里来了。<br> 在试着做出那个决定之前,史珂就知道自己会多么孤单。他可怜自己。如今走在通往衰老的路上,害怕孤单了。四年前走出京城,凡能携走的杂七杂八他都带回来了。这儿是他的出生地,他就待在这儿了。京城太喧闹,一辈子都太喧闹。叶落归根吧。老友们为他惋惜:今后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他笑而不答,只顾收拾东西。其实京城已经没了亲人,早就没了。而在故土,他至少还有一位侄子呢。离京前一年他去了一趟美国,哥哥史铭在那里定居。他一说自己的打算史铭马上赞同:回老家吧,京城有什么好待的。你回去,史东宾会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br> 史东宾是史铭与前妻之子。正如史铭所料,侄子对归来的叔父处处殷勤。史珂并不喜欢这样,因为他知道殷勤这种东西不能持久。果然,一年之后他就不得不从侄儿家搬走了,搬到海边的一所孤屋中。屋子建在河湾一带的防风林中,原属祖产,早已破损不堪。侄儿当时一边咕哝“简直是疯了”,一边抓起手机呜呜哇哇一阵。只几天时间,他手下的人就把一个陋屋修好,把老人请了进去。<br> 真正是傍海而居。突然而至的沉寂中,史珂知道有什么新东西要开始了。这年头无边的时髦围逼过来,新东西却不多。他欣喜四顾,觉得崭新的时间正从脚下滋生。好好回忆的日子来到了。它在京城没有,在浅山市侄儿的家中也没有。市区与河湾之间有两个村落,所以这儿偶尔有人捕鱼采菇。这些人并不妨碍回忆。他刚刚与之对应几句,他们立即惊呼:“京腔儿!”史珂心头一动。他已经在一年多的时问里努力操练故语,总是毫不留情剪除儿化音,最大限度减少卷舌动作,可最终还是被人指认。这很像在京城的情景——当年无论怎么用力,人家一仄耳朵就明明白白。一个主要元音的轻微卷舌处理不当,外地人身份即暴露无遗。融于京城的急切和苦恼一直伴随,直到今天,直到全部努力戛然而止——一种逆向过程却刚刚开始。一个人到了这把年纪还要含辛茹苦消除自己的声音标记,真是生之烦恼啊。相互熟悉一些了,对方难免要询问做些什么啊妻子儿女啊。只能沉默。好像多年来第一遭面对这样的问题:四十余年置身于一个显赫的学术机构,却没有一本著作。妻子已经辞世;儿女,没有。他的脑际倏然闪过一位西方诗人哀伤的句子:“为那无望的热爱宽恕我吧/我虽已年过四十九岁/却无儿无女,两手空空,仅有书一本。”这诗用在自己身上还需几处改动:改年龄;“仅”改为“没”。这一改何等了得。他闭上眼睛。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旁观者,一辈子都在看、看。我的无用的人生啊。史珂曾试着把“旁观者”三个字换成“目击者”,心头一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