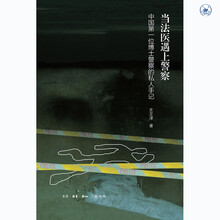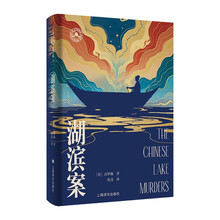贝达!是他回来了。这怎么可能?他不是被国王逮捕并放 逐了吗?不是号称王室的告示里已经宣布他死亡了吗?然而他 就在这里,站在他以前待过的房间里,怒气冲天俨然是上帝的化 身。他是怎么回来的?难道弗朗索瓦国王允许他回来,还是他 强行违抗了国王的命令? 他身材高大而干枯,长长的鹰钩鼻,双唇薄而缺乏血色。他 身着栗色长袍,腰系多节的土黄色腰带,双臂交叉拢在袖子里, 缓缓地穿过房间。在诵经台边上,贝达站住了,扬脸直视阿莫 里。黑色尖顶帽下是他的一头白发,他肤色苍白黯淡近乎透明, 但他的双眼在摇曳的烛光中显得尤其黝黑可畏——用学生们的 话说,这是一双足以窥视灵魂的眼睛。贝达一言不发,一动不 动。阿莫里感到几乎察觉不到他在呼吸。这等光景简直超越时 空,令人油然而生敬畏。 从私人住处又走进来一位男子,身着黑色长袍,腰系黑色腰 带。他比贝达要年轻,身材稍矮一些,略显富态而又不致给人颟 顸之感。他容貌平和,甚至不妨说是英俊;脸上没什么皱纹。这 么一张脸的主人应当从未经历过负罪感或良心负担之类的玩 意,因为他相信自己一向秉公办事。他的风度是平易近人的,简 直可以说令人身心愉悦——当然,这想必与他的实际职责无关: 他通常做的事情就是把男人女人投进大牢,严刑拷打,甚至折磨 致死。 他就是欧莱,宗教审判官。他曾经在蒙台居布过道,所以阿 莫里认得他。在布道中欧莱警告人们,蔑视正统教义是危险的; 他讲了很多故事,关于烙铁、割舌头还有火刑柱上的生不如死。 贝达开口说话了。“看到我令你很吃惊,嗯?”和被流放前相 比,他的声音变得更嘶哑刺耳了。他的双唇只是轻微地颤动,但 话语去异常清晰,充斥整个房间。“难道你以为凭国王就可以违 抗上帝的意志吗?”他顿了顿,吸口气。“我在这个位置服务了有 十三年了,自从我主耶稣基督离去、真正的宗教创立至今,教会 还从未面临过像如今这样严重的危机。为了保护天主教会不被 破坏,我不得不时时刻刻都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我这么做既不 是为国王也不是为教皇,而是为上帝本人服务。你认为我过 分吗?” “不,教师,教会需要你,”阿莫里坚定地回答,心里忆起在贝 达的鞭挞下丧生的学生们。 “人类世界患病了,”贝达语声低沉,仿佛正站在山巅布道。 “这像是一个毒瘤,诱惑民众,中伤学者,贬损教会力量,公然制 造分裂,违抗歪曲《圣经》,诽谤亵渎圣灵。播下毒种的是敌基督 路德,一个愚蠢的德国人,却自以为比古往今来一切神职人员都 更睿智多识。他竟敢用自己的见解否定先贤。更有甚者,他还 妄图废除来自教会的神圣教令,仿佛上帝只令他一个人有权做 出这样的判断:对于信徒的获救来说,何为必要。” “我们宣布,”贝达提高声调,像是怀着怨恨开始宣判,“以我 们的名义:这等邪恶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祸害,它必须完全彻底 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投入火焰,”贝达下颚的肌肉纠结抽搐着, 但他双眼眨也不眨地瞪视着阿莫里,“无论它出现在何时何地。” 诅咒结束,贝达的呼吸才轻松了些,每次呼吸的末尾都有轻 微的喘息声隐约可闻。他伸出一只手搭在诵经台边上支撑身 体。阿莫里这才感到自己面对的人已经上了年纪。怎么会这样 呢?在流放生涯中,贝达想必已重病在身。这样一位巨人难道 也在走近死亡?阿莫里会在某种意义上陪伴他走过最后的 路吗? “我要离开了,”贝达嘶声低语道。“接下来欧莱教师要对你 说的一切内容都经过了我的首肯,而且必须严格保密。倘若泄 了密,那么给你再厉害的惩罚都不过分,丝毫不过分——明白?” 阿莫里点头。……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