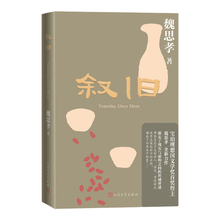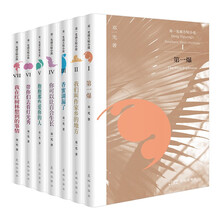那天窗外下起了雨,天地之间呈现出一片乌涂涂的雾霭。我坐在旧金山那座廉价公寓楼的房子里,在闷头写作,同时想着心事。窗外的雨点拖着长长的雨线从天上落下,把灰灰苍穹编织成了银白色的网状。
那是来美国的第三个年头,虽然生活上已经基本适应,但写作还是无法进入状态。所以写作时的感觉像是在黑咕隆咚的山洞里爬行,找不到洞口。由于威廉对我到美国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寄予了厚望,所以即使爬行也要一往无前地往前走。
和大部分作家不同,我写小说多是为了享受其中的过程,而并不在乎小说写成以后的结果。如果一次写作能够给我带来激情喷涌的快感,那么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非常值得的。也正是由于我只管埋头耕地而不顾收获的马大哈态度,所以我必须有一个像威廉这样的经纪人,以便有人给我的小说料理后事。
千万别问我《情徒》这个书名的来历,因为它是威廉起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据威廉讲,这个书名是他在梦中受到的启发想出来的。在我动笔之前,威廉给小说打好了框架,定好了基调,除了书名是他拍板定下来的之外,他还向我提出了“三要”的原则,即:内容要奇特,文字要新颖,意识要超前。虽然他嘴上说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谨供你参考,可实际上他的话像道军令一样,对我具有“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威力。
显然,威廉是把《情徒》看成他的大手笔的第一步了。“既然是第一炮,就一定要打响喽。”威廉对我说。
关于威廉,关于他的大手笔,还有我们之间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要讲的故事可以讲上一千零一夜。对了,差点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王大宝,英文名字叫查理斯。王大宝是在中国时叫的,而查理斯这个名字则要面向美国。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天色更阴了。也许是情绪的关系,或者是心理的作用,我觉得外边的天空在慢慢地收缩,旧金山的廉价公寓楼的房子也显得越来越小。
正当湿淋淋的雨水拖着细细的白线折射进我的眼睛里的时候,我的意识正沉溺在一个非常暖昧的情节里。这时门外有人在高声叫喊查理斯,随即房门哐啷一声开了,把我吓了一跳。我抬头一看,闯进来的是冈布娜。见到她风风火火的样子,我的脸立刻拉了下来。看来今天八成是我倒霉的日子。
不是我说什么,世界上的女人真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她们中有的能让男人睡不着,有的则让男人醒不了。还有另外一种女人更厉害,她们可以让男人睡着的时候像醒着,而醒着的时候又像睡着了。冈布娜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说到冈布娜,我有很多话要说,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首先是她的品种,这包括她的种族和她的性别,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她不是女的,我们之间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纠葛;如果她不属于亚热带的黑种人,我们的关系也会简单得多,省事得多。多年前,我和威廉在中国的滨城初次见面,虽然彼此很陌生,有些方面甚至是格格不入,但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默契。我们虽然各有各的属性,就像酸和碱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但碰在一块儿就会发生中和反应一样。
当时威廉正铆足了劲儿要搞出他的什么大手笔,可又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所以他一见到我,就“啪嚓”一下生出了打造一个“跨国作家”的想法。好在威廉是做事的人,只要认定了一件事,他就会全力以赴去做,绝不会让好主意变“馊”了。作为大手笔的第一步,他得先要把我变成美国人,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和美国挂钩,借助美国的国力和霸道的国际形象,他的想法才是大想法,他的气魄才是大气魄,要不然,还算什么大手笔?仗着威廉早就是美籍华人了,而且他所做的中美生意发展得相当不错,他说他的腿虽然短,但能够横跨太平洋,言外之意是他脚下踩着两条船,一条船是中国,一条船是美国。
威廉对我说:“得先给你找个美国女人,让你结了婚,拿到美国绿卡,剩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威廉说话的时候很认真,我还没有看过说话这么认真的人。好在作为生意人威廉手里有的是“渠道”。
那时候我在文坛上还很雏,还没有完全展开拳脚,因为从小就爱听鬼故事,还喜欢攒些蛐蛐罐鼻烟壶之类的土特产,所以我选择了民俗作家作为我的发展方向。对了,我的代表作是《夜壶的传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