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
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外阴”这个词,就像一些孩子说“屁股”、“蛋蛋”或是“呕吐”那样。虽说算不上粗口,但我知道,它有一种无形的尖角,能令大人们呆若木鸡。对所有家庭而言,“外阴”是那些具有双重含义词语中的一个:既可以描述人体生理构造的某个部分,或某种基本的身体反应(比如呕吐),也用来表达飘摇的心绪与眷眷的情思。
在我家,却独独不然。
记得一日午后,我在罗莉·麦肯纳家玩耍,她母亲正招待一个来自蒙彼利埃 的朋友。那是一个罕见的佛蒙特州夏日,天色蔚蓝得近乎虹霓般夺目。那种蓝色往往在一月份才得一见,那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邻家柴火炉中的青烟仿佛在冒出烟囱的刹那冻结。但这样的天色在六七月间却绝少出现。
同她一样,麦肯纳夫人的这位朋友也在州教育部门工作,她们在麦肯纳家砖砌露台上,围坐在铁艺小桌旁,啜饮加薄荷的冰茶(薄荷来自我母亲的花园)。即使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个露台也优雅得不合时宜。我走上前去,津津有味地描绘辛西娅·沙博诺的分娩经过:
“沙博诺夫人的宝宝约四公斤重,但我妈妈按摩阴道以使肌肉松弛,这样会阴就不会撕裂。如果宝宝重量有四公斤左右,大多数人都要做会阴侧切手术——就是把一个女人从阴道到肛门的那段会阴剪开——但沙博诺夫人却没做,她的外阴好好的,胎盘也紧接着诺曼(他们这么叫那个新生宝宝)大约两分钟之后就排了出来。我妈妈说,那个胎盘也好大,现在被埋在他家前院,沙博诺先生种的那棵枫树下面。我爸爸说,希望他家的狗不要把胎盘挖出来,但它确实可能会——我说的是狗。”
我大约9岁,那时麦肯纳一家在佛蒙特州只住了一年多一点。他们在我8岁生日当天,从纽约城郊的威斯特彻斯特 搬到我们镇上。当搬运货车缓慢驶上门前的小丘,我告诉父亲,希望那辆车可以左转驶进我家的车道,卸下我的礼物。
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还不如期盼月亮从天而坠,掉在我们的屋顶上呢。
我从未去过威斯特彻斯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麦肯纳一家来自一个比瑞灵顿讲究得多的地方,那个露台便是不言自明的铁证。他们比我们佛蒙特州人要冷淡和拘谨,与我父母那些朋友相比尤其如此,那些人喜欢和解放通讯社 的社员厮混,并将爱珠 视为深刻的政治理念。我喜欢麦肯纳一家,不过,当罗莉将我介绍给她母亲时,我曾有些许疑虑。若在佛蒙特州最大的城市伯灵顿,他们没准活得不错,但在瑞灵顿这样的小村庄里,我想她家或许呆不长。但我错了,麦肯纳一家过得挺好,尤其是罗莉。
镇里那些父母禁止他们的女儿去我家玩。一些人仅仅是害怕母亲一时找不到保姆,将他们的女儿抓来充数;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被母亲称为干预药物的奇怪草药和酊剂里,混合了大麻、大麻麻醉剂和致幻的蘑菇。而麦肯纳一家却似乎毫不在意我母亲是个接生妇。
对九岁的我而言,告诉麦肯纳夫人和她朋友,诺曼·沙博诺如何从他母亲的产道中出生,与向父母汇报学校功课、恳求十二月里从桑迪·德莫瑞斯家后面的小山滑下一样稀松平常。
等到十四岁那年,母亲被告上法庭。我开始厌倦拿关于自然生产的丰富知识,或者那些在家接生的惊险故事来吓唬大人。另外,我也开始明白,十四岁少女言谈中“外阴”这类的字眼,要比从小女孩的口中说出更不讨人喜欢。
此外,十四岁的身体,早已开始了从孩童到少年的转变:五六年级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穿少女文胸;成为县法院常客的近一年前,我开始来月经。而一想到,一个四公斤的东西会从我两腿间的小小孔洞中出来,我就感到一阵恶心。
“我就是想不通,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从那么小的东西中通过!”我固执己见。父亲有时会摇摇头,评论道:“糟糕的设计,不是么?”
如果母亲在场,她会一成不变地反驳:“才不是!那是一个神奇而美好的设计,完美无缺。”
身为接生妇,我想母亲只好这样认定,而我却不然。如今已三十岁的我,依旧无法理解,无论它是爬行、蠕动还是猛冲,那么大的婴儿怎能通过如此细狭的管道?
尽管母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位朋友接生,但从我八岁起,无论白天黑夜,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个固定的保姆又在匆忙间无法赶到,就由我陪她接生。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母亲怎么办,但想来,她总能找到一个人应急。
我能记起的第一场接生,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雨之夜。大概是初夏的光景,六月份的第一或是第二个星期,那时我正上二年级,学期已近尾声。那天,我第一次听见母亲喃喃说出“头出来了”这句话。之后,经过想象力的加工,便成了一个婴儿头戴生日帽,从产道被挤出的情景。
母亲认为,婴儿更有可能在乌云密布的天气里降生,因为那时的气压比晴天低。那天黄昏,母亲和我在门廊上吃晚饭。她望着天边聚涌的乌云,对我说,洗过碗碟之后,或许该问问谁晚上能有空帮忙接生。那晚,父亲身在纽约州那侧的尚普兰湖 畔,在那里,他为一所学校设计的数学科技馆将于第二天破土动工。那时,离父亲创办自己的公司还有三年之久,所以那座建在半山腰的建筑并不是他的个人项目。不过,多亏了父亲,它才没被建成北美防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模样。
艾米丽·乔伊·派因(或者叫她E.J)是我目睹分娩的婴儿中的第一个。她的出生被称为“顺产”,但在当时还有一个月才满八岁的我看来,可绝非如此。那天,大约晚上十点,大卫·派因给我家打电话。母亲还醒着,并很快接了电话,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依旧毫无察觉地酣睡。所以对我来说,母亲吻我额头、将我唤醒时,艾米丽的出生才算真正开始。我记得床边的窗帘伴随徐徐微风,在母亲和我之间扬起,那时天色已变,雨却尚未落下。
我们到达的时候,洛丽·派因正坐在床边,肩膀上松松地披着一条轻薄的棉线毯。床上其他的东西,比如毯子、床罩和床单之类,都已经移开,在地板上堆积成一座小山。床头有几个圆滚滚的枕头,看起来像是旧沙发的靠垫。床垫上铺着一张床单,上面印着许多梦幻感的向日葵,满眼泪滴状的花瓣和散发光和热的太阳,如果用在又大又丑的浴帘上,这样的图案或许更合适。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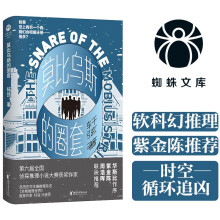

——《华盛顿邮报》
“法庭的场景……货真价实,但波杰里安同样精于演绎……更安静的独角戏……一位慧心独具的作家。”
——《波士顿环球报》
“珍宝……兼具优美文笔和写作激情的小说带给人难求的愉悦。”
——《波特兰俄勒冈人报》
文采出众而震撼人心……如果你珍藏着一本翻烂了的《杀死一只知更鸟》,那么就千万不要错过此书。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