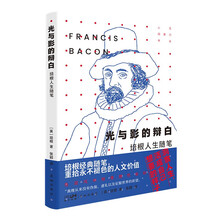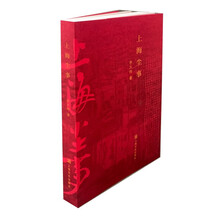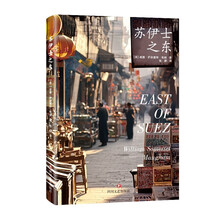杨绛先生在钱锺书先生和他们的独生女儿钱媛相继去世后,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写出了家庭回忆录《我们仨》。书还没上市,已有多家报纸选刊部分章节。我迫不及待地等着拜读,不仅因为钱先生是我从青年时代就景仰的大师,而且我还幸运地与钱先生有过两面之缘,通过几次信,有过几年短暂的交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一生,如果有这么两次与敬仰的智者谈话,所愿已足!”
一
八十年代初,我在上大学期间开始接触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先是《围城》,再是《管锥编》,对先生的博学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九九○年,我在旧书店淘到一本徐燕谋先生在四十年代末编写的英文散文选读,书前有钱先生的一篇英文序言。我知道,钱先生和徐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徐先生的旧体诗集也是钱先生作的序。当时我正在编《文汇读书周报》,就约请徐先生的学生陆谷孙先生翻译这篇文章。陆先生一口答应,但要我先征得钱先生同意。我冒昧写了一封信到社科院文学所转钱先生。过了几天,收到钱先生的回信,信中说:“我少年所作小文,均不值保存,自己亦早忘怀。承寄示一篇,不过其中末例。似不必劳谷孙先生大笔迻译,所谓‘割鸡焉用牛刀’。贵刊并无‘稿荒’之患,何至出此填空补白之下策!?”
第二年下半年,我约请上海师范大学的林子清先生写了一篇回忆钱先生在暨南大学时期的文章。为了慎重起见,我把校样寄了一份给钱先生,请他定夺。钱先生在回信中说:“子清同志此文实可不写。盛情可感,而纪事多不确实,或出记忆之误,或出传闻之误。遵命删改一下,请子清同志过眼,并请他原谅。回忆是最靠不住的,我所谓‘创造性的回忆’。子清同志是忠厚老实人,对于暨南同事中的‘人际关系’实况,不甚看透,故把詹、李、方的话也删掉了。”所谓“詹、李、方”,指的是文中提到的当年暨南大学的教师詹文浒、李健吾和方光焘。钱先生在校样这一段的旁边批道:“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钱先生不仅把林先生的文章删去五分之一,还在很多段落旁作了批注,如林先生说有一次他看到钱先生在读《胡适文存》,读得哈哈大笑。钱先生删去这段话,在旁边写道:“恐无此事,《胡适文存》我在中学时阅过,到六年前才查一句引文。”后来我把钱先生改定的校样给林先生看,林先生扯着大嗓门说:“我可以对天发誓,钱先生那时看的肯定是《胡适文存》!”尽管如此,我还是尊重钱先生的意见,把那段话删去了。文章中还提到钱先生讲文学批评课时说,他的讲课内容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有相似之处。钱先生删掉了这段文字,并在旁边写道:“并非事实,恐系误记。我只说朱先生的书主要利用法国Delacroix的PsychologiedeLArt,而大家不知道。”钱先生把文中讲到他翻译毛泽东著怍的几句话也删了,旁批说:“此事不宜讲。译事乃‘集体工作’,故译本上无参加人姓名,中央政策,我怎好出头居功!”从报上选刊的章节看,杨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倒没有回避此事,而有详细叙述,还说到钱先生在翻译毛选时,发现原文有个错,他坚持说:“孙猴儿从来未钻进牛魔王腹中。”负责毛选翻译工作的胡乔木从全国各地调了不同版本的《西游记》查阅,证明钱先生的话是对的。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两句。
二
钱先生有一次在电话中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但是下过《管锥编》这样一只金蛋的“母鸡”,谁又能不想见呢?
终于让我逮着一个好机会。一九九一年秋天,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出版了上卷,因为书名是钱先生题写的,所以我就自告奋勇向陆先生提出,给钱先生送样书。凭词典这块“叩门砖”总可以叩开三里河南沙沟的钱家大门了吧。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钱先生答应召见。约定时间,我捧着词典来到钱先生家。出乎我意料的是,钱先生不仅没让我难堪,还特别热情地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问我多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