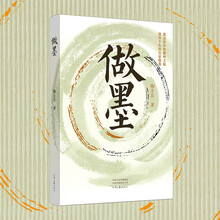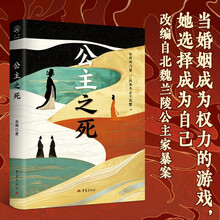现在,他回去时,人更白些,也更轻些。
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骑士的男仆和厨师鬼鬼祟祟地在他们中间把一个瓶子传来传去,一边和行李搬运工聊天。九月的太阳有一圈光晕,越发明亮。一阵东北风朝白厅大道刮过来_片烟云和煤味儿,盖过了清晨通常飘着的恶臭。街上能听到其他马车、小车、手推车以及起程的驿递马车发出的咔嗒声一拉第一辆马车的一匹小马急躁地走动着,马车夫勒住辕马的缰绳,劈劈啪啪地挥着鞭子。查尔斯到处找他舅舅的贴身男仆瓦莱里奥,以便在仆人中间恢复秩序。他皱着眉掏出了表。
几分钟后,骑士从旅馆走了出来,和他一起走出来的是点头哈腰的旅馆老板和老板娘,还有瓦莱里奥;瓦莱里奥拿着骑士最喜欢的小提琴,琴放在一个华丽的皮箱子里。仆人们立刻安静下来。查尔斯站在那里等待示意,他的长脸表情显得更加警觉,让他们俩看上去长得越发相像。骑士停住脚步,抬头看了一眼灰色的天空,呼吸着恶臭的空气,心烦意乱地掸去他衣袖上的一个污渍,大家这时毕恭毕敬,一声不吭。接着,他转过身去,朝他外甥淡淡地一笑,后者快步走到他身边,两人便手挽手,朝马车走去。
查尔斯挥手示意瓦莱里奥让到旁边,他伸手打开门,让他舅舅上去,弯腰,进去,然后,他跟着递过去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骑士在铺有绿色天鹅绒的座位上坐好时,查尔斯朝里面倾过身体,带着真诚的爱与关切,问他舅妈感觉如何,同时,最后与他们道别。
车夫和左马驭手各就各位。瓦莱里奥和其他仆人上了那辆大一点的马车,这辆车发出叽叽嘎嘎的响声,离地面又近了几英寸。查尔斯,再见。对着充斥着煤味的空气(这种空气对哮喘病人十分危险),在一声声出发和催促声中,窗子关上了。一扇扇大门都开着,物品和牲口,仆人与主子全都一窝蜂地涌上街头。
骑士脱下琥珀色手套,漫不经心地弹拨手指。他即将返程,事实土,他盼望着这一旅程--他是靠发愤努力才飞黄腾达的一盼望着回程会给他带来新的邂逅和收获。他跨上马车的那一刹那,离别的焦虑就已经消失,变成离开的兴高采烈。但_是,他是个体贴的人,至少对他妻子如此,他喜爱她,一如他一直喜爱任何其他人一样,所以,他们坐在窗子紧闭的马车里,慢慢地经过越来越忙碌的街道所发出的喧闹声,他感到越来越快乐,但他不会说出来:他会等凯瑟琳,她闭着眼睛,半张着嘴巴在浅浅地呼吸。
他咳嗽一声--代替一声叹息。她睁开眼。她太阳穴青色的静脉在跳动,但这不是讲话。文仆坐在角落里一张矮凳上,红润的脸低着,在看女主人给她的艾岚的《给未曾归正者的警告》,别人跟她讲话的时候才允许她讲话。他伸出一只手,找他屁股后面的一个箱子,里面放了折叠的皮革封面的旅游地图册、文具盒、手枪和一本他已经开始阅读的伏尔泰的作品。骑士没有理由叹息。
这样一个温和的日子这么冷,真奇怪,凯瑟琳嘟哝了一句。我怕--想要极力讨好,她会先说一句克制的话,然后再自我驳斥一旬--我怕我是已经习惯了我们那些个热死人的夏天了。
你这次旅行可能是穿得太暖了,骑士高声说了一句,带着点儿鼻音。
我祈祷我不要生病,凯瑟琳说着,拉过一条驼毛披肩盖在腿上。能不生病,我可不愿生病,她又自我更正了一下,她笑着抹了抹眼睛。
和我们的朋友,尤其是和我们亲爱的查尔斯分别,我也感到很伤心,骑士轻轻地回答道。
不,凯瑟琳说,我回去不是不开心;尽管我害怕飘洋过海以及接下来的艰难--她摇摇买,停顿下来--我知道,很快我呼吸起来就会更容易些。那空气……她眼睛闭了一会儿。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回去你很高兴,她补充了一句。
我会想念我的维纳斯的,骑士说道。
尘土、臭味、喧闹都在外面了--如他们驶过的马车投在店铺前门的门窗棂玻璃上的阴影。在骑士眼里,伦敦成了个景致,时间退人空间之中。马车摇晃,挤撞,吱嘎作响,东倒西歪;摊贩、推车叫卖的小贩和其他车夫喊叫,但是和他将会听到的叫喊声相比,是另一种腔调;这些还是他同样熟悉的街道,他可能横穿马路去参加皇家学会的一个会议,顺路去看看某次拍卖,或者去拜访一下姐夫妹夫什么的,不过他令天不是要横穿,而是穿过这条街--他已经进人了一系列辞别{了结、特许的最后的观望的王国之中,它们倏忽之间便写人旅行日记成为记忆;期盼的王国。每条街,每个喧闹的拐角都传达出一种信息:曾经的,将要的。他此刻在两种强烈的欲望中间摇摆不定,既想观看,仿佛要将所见铭刻在脑海之中,又欲将他的所有感觉都限制在凉爽的马车里,好好想一想自己已经离开(他的确如此)。
骑士喜爱怪人怪事,可能在不断增加的人群中找到了许许多多,成群的乞丐、女仆、小商贩、学徒、顾客、小偷、兜售者、挑夫、差役,他们在移动的障碍物和车轮边或之间来回穿梭,非常危险。在这种地方;甚至连那些个倒霉蛋都是一路小跑。他们不会聚众,不会成群;不会蹲占一个地方,也不手舞足蹈,自娱自乐:这里的人群与他正返回的城市的人群有诸多的不同,其中的一个区别可以记下、加以思考一如果尚有理由记下的话。但是,思考伦敦的喧嚣与拥挤可不是骑士的习惯;一个人不大可能认为自己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他的马车在吵吵闹闹的推车水果摊贩和脾气暴躁的磨刀师傅的车子之间停了一刻钟时间,在此期间,他没有注视那个红发盲人,后者胆大妄为,横穿马路往前走了几码,他的棍子戳在他面前,根本就不管那些开始向他逼近的车辆。移动着的马车里面香气四溢,层层叠叠堆满了专门配备的足够的物品,让五官应接不暇,似乎在说:别看。外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一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