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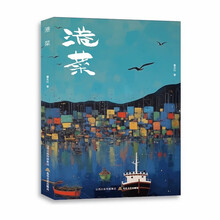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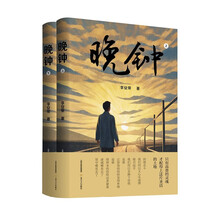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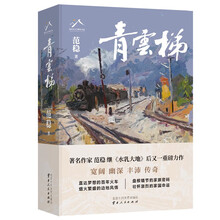
生活真的能将一个人的意志磨灭吗?记忆里的伤痛是不是只要拔掉记忆这根刺就可以让自己安抚呢?好像记忆的存在总是折磨着又感动着我们自己,只是时光的流逝,无法抵挡的命运的轮盘,始终在把每一个陌生人拉扯着生硬地逼上感情流离失所的境地。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爱呢?可惜因为那颗跳动的心脏,牵扯着神经每一吋细腻的迂回。当我爱上你的时候,我甚至无法摊开手心;你抛下一缕阳光碎屑,都会轻易地割破我掌纹的细腻。
被称为“中国具灵性的双语词作家”
擅长中英文写作的她,更擅长将文字雕刻在音符的韵律下。
这是她的第一部长篇中文小说,写作了整整三年,一部小说曾经被她在八个国家的穿梭中来回反复的敲击。她说,这是一部“新叶”,每一个思纹都要细细缝合,密密接洽。
《西班牙的陌生人》送给你,你总是自以为自己已经干枯了心灵,你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就要这样孤独的老去,你总是拔不出脑海里那些记忆的刺……
可是这一次,你还可以再相信一次吗?再相信无悔地爱一次!
“安薇,一如既往,你手里的就是你有的”
“安薇,如果有不开心的事情,就丢给我,我去替你记着。”
如果她可以打开尘封坚硬的心扉,爱情的发生,没有什么是奇迹!
西班牙的土地上,一个中国女人,重现爱情的绝唱!绝对足矣震撼心扉的灵魂小说!
二十一世纪初的西班牙南方,穆尔西亚城,别有风情又匆匆庸碌的小镇上,几个漂泊的异乡人写下了荡气回肠、生死相随的寻找心灵归宿的传奇。伤心的中国女画家安薇在三年里反复画着同一张面孔。这座小镇曾经有一首风靡一时的歌《ThePromise》,而歌曲的作者却在几年前的一段波折的往事中离奇身亡。从此,这座城镇陷入了庸碌与沉寂。
一名失忆人被海水冲到岸边,被医院院长的女儿救起,取名为默多。一年后他从医院逃了出去,因为时而发作的疯狂头痛中始终萦绕着一个女子的名字,引诱着他四处流浪、追寻。
性格古怪、桀骜如男孩的安薇在穆尔西亚偶遇流浪汉默多,并将其暂时收留在家,在两人卸下初的心防后渐渐成为了朋友,进而在这座被冬天笼罩的城市相依为命。
默多与安薇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谨慎而惶然地探索着自己的命途和对方的心意,他们性格中的防范意识与自尊又不时带来伤害与矛盾。医院院长女儿琳达的追寻而来则为他们尚未开始又充满不安的恋情带来了摧毁式的打击。
两个含着珍珠的蚌,一旦相爱,必将要残破一道道伪装的坚强,释放内心柔软的力量,但是珍珠总是在里面,风干的力量只会将爱情永恒的结晶。
一个中国女人在西班牙的小城市里,经历的爱情传奇故事。
该有多幸运,才能够有幸选择到底该折磨、还是该珍惜?
如果你知道爱有多珍贵,也许你会对它另眼相看。
每当他们的车“吱”地一声刹在“红蛇”酒吧门口时,马诺罗总是第一个跑出来,冲他们大声打招呼,扯高嗓门嘘寒问暖。
这吉普赛人总是那样红光满面、情绪高涨。他的每一分钱都来自酒吧,不出一天,他的全部所得也会源源不断地回到酒吧的钱袋子--老虎机和酒中。这简单的一入一出带给马诺罗难以言喻的快感。于是他就长在了酒吧里生根发芽。对于他来说,来此聊几句外加多干几杯,听听能制造逗人噪音的外地小乐队的音乐,实在是太迷人了,也难怪他每次都能如期而至,而且不由分说就开始帮那些长发小伙子们搬运沉重的音箱。
他又来了,一如既往。“这次怎么走着就来了?今天人不多--家伙呢?”马诺罗油光锃亮的黑发夹杂着银丝,笑得喉头直颤。迭戈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能一天到晚都那么兴致盎然,不自觉地却被他带动得言语缓和了些。“今天不演,”杰洛在卡洛斯走出来的瞬间瞥了他一眼,“就来看看。”
卡洛斯倚在门口,假装什么都没听见,“红蛇”酒吧自从被他盘走以后,摇滚演出少了些,酒却没少卖。今天天气不太好,卡洛斯踱出来摆摆样子,然后就扭头钻回屋里去了。马诺罗失望的声音顿时降了半个八度:“我还以为今天是你……哦,那就一起看看吧!迭戈,等啤酒减价的时候我一定请你喝个痛快。”他迅速恢复了兴致,声调又高了起来:“杰洛,一起来吧?”
“留着钱给你孩子买糖吧!”杰洛扫了一眼这两个人,转头低声咳嗽了两声。演出还没有开始,大概还有一两个小时,卡洛斯懒洋洋地在吧台的长条桌尽头窝着,短粗的手指头杵着浓黑的眉头,故作哀愁地跟刚到不是太久的吧台小姐絮叨着。女人们在天冷的时候会无一例外地找个高调的机会当众脱掉毛衣或披肩,露出邋遢的镂空上衣或者紧身的低胸小衫。男人们大都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还有摩洛哥人,这些皮肤粗糙赤红的人眼神像鹰一样锐利和苍凛。吹嘘着的,寒暄着的,西班牙女人的嗓门总是大得惊人,好像交通堵塞时候的汽车喇叭一样。酒吧里的人忽然变得出奇的多,也许又是个红日(西班牙各个地区的各种公共节假日)。天气凉了,人们去不了海滩了,就都挤到酒吧来了。只是--今天这么些人,乌央乌央的,看着很是闹心。那名不见经传的小金丝雀乐队,还偏偏有这么多人给捧场。杰洛不知不觉就被人群顺着给挤了出来。一阵冷风过脑,他打了个激灵。
“希望迭戈把握好,别惹什么麻烦。”然后他转身向外走,去马路上吹吹风。马路上只有一辆车,从远到近,一辆涂着过时的漆,布满划痕,底盘又很高的车。车的钢板足有一只大手掌那么厚,而且看起来饱经沧桑--这辆车应该用来贩运军火!或者至少可以用来拉那些笨重的乐器设备。杰洛看着这辆金属野兽在毛玻璃一样的刚刚被吹散的雾霭中爬行进视野,他的眼睛被刀子一样的风吹得.生疼,却眨也不眨一下--这是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和迭戈决不一样,他没有迭戈那戾气十足的孩子一样的脸,也没有迭戈苗条的身段,他高大,有粗壮的手臂和宽大的手掌,眼睛很明亮,在浓密的眉毛下低低地压着,深陷的眼窝里进射着坦荡的斗志--他应该是能够保护需要他的人的那种男人。早在十年前,他就能三拳两脚替迭戈解决最难搞的街头混混,也能帮助邻居修理屋顶,还能帮隔壁的施工队开斗车、挖地基--尽管是偷摸尝试被施工队发现后通知了家人并且挨了揍。
这双拳头曾经带给过他血的快感,也带给过他耻辱。因为带着股方刚血气,没人敢轻易挑衅他,可又因为力气不够,因为自己太弱小,他也没能成功地把母亲从医生那里抢回来,只能眼睁睁地放任他深爱的这个女人如柳絮一般随风而逝,然后被推进一个大门紧闭的冰冷的房间里,和很多人并排躺在了一起。如果可以,他随时可以战斗,可以一拳打碎敌人的头颅,如果可以--而在这个年代,真正的战争是无形的,敌人是柔弱而且会哭泣的。
生活会把你裹在一床潮热的缝满绣花针的棉被里面,让你在透不过气的温热中像个蠢货一样就这么伤风瘫软,似乎连为自己所在乎的事情去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样的自愿的悲壮剧幕都成了一种幼稚的奢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