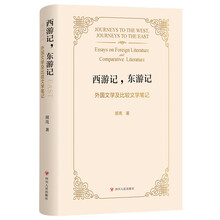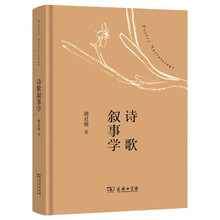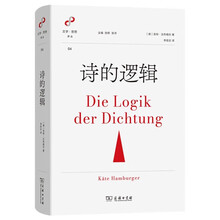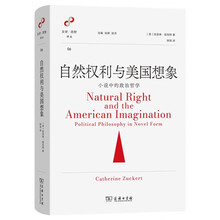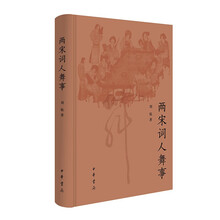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葬花吟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着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天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初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已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侬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整部红楼,这是第一首让人哭出声的诗。
在青春埋葬青春,任花颜埋葬花颜,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深沉、更刺骨的伤呢?
荷着花锄的颦儿,眉间微蹙的女子,每一念及这样的场景,那弱不胜衣的身体仿佛就要委蜕成蒙蒙的红雨,在“花谢花飞飞满天”的弥弥宇宙里和开的花、落的花、飞的花、葬的花一起,如一面一尘不染而又纤薄如纸的镜子,在心爱少年的心尖被哗啦啦地打碎了。
那碎片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她的影子,藏着自己的影子,在等待爱侣抱紧的时候任它刺出艳红的、浓烈的血。痛,便真痛;爱,便深爱。这是我们得自《葬花吟》的所有,美不够美,在你面前任你眼睁睁摔碎的美才是真美。
是的,美永远伴随着毁损,正如轻盈的花永远伴随着污浊的泥,正如骄矜的颦儿永远伴随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世界,正如白天的我永远伴随着夜晚的你。
尽管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会嗔怪这样无常的宿命,但看得破又如何,谁又能从这无常的宿命里拈得一枝不谢的花么?
所以惜花总是轻薄语,葬花才是真惜花。这个亘古相传的秘义只有故事中的人才能懂得,所以颦儿懂得,宝玉懂得,书中更无第三个人能够懂得,书外的你我究竟能够懂得几分呢?我们若懂得,便也是故事中的人了。
这就是《葬花吟》,只属于颦儿与宝玉的私语。我们看得到,却看不见;听得到,却听不见。我们所知的全部,也仅仅是镜子碎片上倒映出来的点点滴滴罢了。
但就是这带伤的、带血的点点滴滴,便赢得了我们最真挚的仰视与最迷蒙的动心。
是的,当我们抽离出故事,站在世俗,我们便知道:虽说“文无第一”,但在所有的红楼诗词里,这首《葬花吟》却是公论的冠冕。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它说:“千古红楼第一诗,伤怀唯有落花知。锦囊艳骨犹无主,已是香丘月堕时。”可以说,一部《红楼梦》的风骨,就在这《葬花吟》里得到了一次华丽无央的预演。
《葬花吟》用的是初唐歌行体,初唐诗人正是用这样一种体裁,以清灵的铺陈洗净了六朝的侈靡,其中代表便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而这样的一座顶峰在一千年来以孤高的姿态俯瞰了太多的追慕者,直到《葬花吟》的出现才“差堪与之比肩”。
葬花主题得自明代历史上一位真实生活过的才女,据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引《弘雅堂外集》,吴江叶氏琼章月府侍书女也,卒后从泐师授记。师曰:“既愿皈依,必须审戒,我当一一审汝,仙子身三恶业,曾犯杀否?”对云:“曾呼小玉除花虱,尝遗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对云:“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对云:“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新绣鸟双双。”口四恶业,曾妄言否?对云:“自谓生前欢喜地,诡云今世辨才天。”曾绮语否?对云:“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裁成幼妇诗。”曾两舌否?对云:“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诗评出短长词。”曾恶口否?对云:“生怕帘开识燕子,为怜花榭骂东风。”意三恶业,曾犯贪否?对云:“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莺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对云:“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奴。”曾犯痴否?对云“抛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泐师遂授记。
这故事来得风趣,故事当中这位可爱而伶俐的女主角就是著名的明代才女叶小鸾,以诗语一一应答自己曾经犯过的佛戒,尽是一副小女生的娇痴。其中痴戒犯的是“抛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正是黛玉葬花之所本。
只是,黛玉葬花痴得哀婉,叶小鸾的葬花痴得娇媚。
佛家以贪、嗔、痴为三毒,叶小鸾坦承自己犯过痴戒,这痴却痴得可爱,卖掉了时兴的首饰,换来了古旧的汉玉,还捐出过脂粉盒子,郑重其事地收葬了落花。这样的痴戒,果然只有才女才会犯得,只有叶小鸾、林黛玉这样仅仅生活在精神世界里的极度敏感的小女子才会犯得,也只有贾宝玉这样天真、天然而不落俗流的少年才能懂得。
的确,最清澈的心只有另一颗最清澈的心才能懂得,就像只有江南小巷的秋天才懂得梧桐为什么叶落。《红楼梦》甲戌本在第二十七回有这样一段批语,大意是说:“我读《葬花吟》再三再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屡屡提笔而不能写下批语。有客人说:‘先生既不是宝玉,如何下笔呢?就算字字珠玑,怕也难遂颦儿(即黛玉)之意,还是等着看看后文吧。’”到了第二十八回,宝玉闻《葬花吟》而生出一番感慨,批语者于此写到:“宝玉听到这首《葬花词》,不去想炼句炼字与辞藻的工拙与否,只是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复追求,悲伤感慨,这是宝玉一生的天性,普天之下没有人比他更懂得颦儿了。昨天阻拦我批点《葬花词》的客人一定就是宝玉的化身吧,若不是他,我便已作了点金成铁之人,笨甚,笨甚!”
宝玉是如何“想景、想情、想事、想理”的呢?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宝玉不经意间听到黛玉吟出的《葬花词》,分明已经由美想到了美的凋谢,由爱想到了爱的消逝,由今日的欢会想到了永恒的孤寂,由眼前的黛玉推及于所有亲密的、美丽的女子,推及于“终归无可寻觅之时”:
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错疑在宝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见饯花之期,正在一腔无明未曾发泄,又勾起伤春愁思,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哭了几声,便随口念了几句。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先不过点头感叹;次又听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呢?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将来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如何解释这段悲伤!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
一个人在悲哀的境遇中自然很容易陷入悲哀的情绪,而在欢乐的顶点有时候竟也会生出一种刻骨的悲凉,这种悲凉比之前者往往深刻许多,因为它摆脱了切身的利害,而指向了人生的终极。
此时的宝玉便是这般,他突然间突破了凡人的眼界,在一个无限广大的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下关照自己眼前的、身边的一切,无论是黛玉、宝钗,还是斯园、斯柳,一向那么近,却突然那么远,他仿佛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星系里,遥遥地打量着自己曾经生活过、也将要生活下去的这个世界,看见星移斗转,看见物是人非,看见他最舍不得的人都会老去,看见他最舍不得的物都会易主。
于是最美好的事物反而变成了最令人悲伤的,因为我们会晓得,今天有多爱,明天就有多痛。我们永远知道“桃李明年能再发”,却永远不知道“明天闺中知有谁”;我们永远知道“明年花发虽可啄”,却永远不知道明年会不会“人去梁空巢已倾”。人有生老病死,世有成住坏灭。石头不挂心,花儿却萦怀;今日的绝色,能否逃过明日白头的一天?
于是我们甚至会生出这样的质疑:命运之所以在今天眷顾我们,就是为了在明天抛弃我们,它之所以给了我们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就是为了看我们如何失去它们。
但我们无力阻挠——我们劝不住花儿的如花陨落,挽不住颦儿的似水流年,施不出全部的好给挚亲挚爱的人,我们吟着“花开易见落难寻”,我们惧怕在最美的年华清醒地洞见了未来,我们同样惧怕那必将降临的未来忽然间不期而至。于艺术,这是至美;于人生,这是至悲。
是的,我们若像宝玉那样在《葬花吟》的婉转里“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便只能看到宿命,还有那悲伤的、忍从的、无能为力的对宿命的屈膝。
这样的资质,是“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的孤高;这样的命运,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凛冽;这样的结局,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凄凉。于是,《葬花吟》作了颦儿的诗谶,也作了我们每一颗不合于俗的骄傲心灵的诗谶。在一场注定的悲剧里,她扬着柔弱而略带几分骄矜的脸,荷着锄头,做着葬花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于世人毫无意义,但于颦儿不然。世人看来,花开易落而人力无方;在颦儿看来,纵然美质终归挽留不住,但人力所能为的,至少要让“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她清醒地洞见着悲剧的结局,但依然执拗而“徒劳”地保持着孤高的姿态。
这是一种痴,一种高贵的痴。黛玉吟得痴了,至于宝玉,“却不道这边听的早已痴倒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