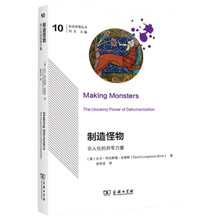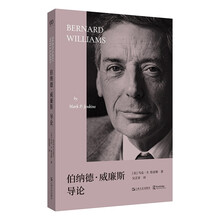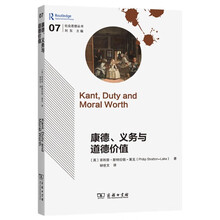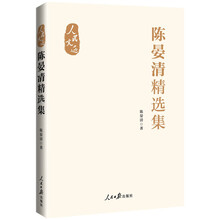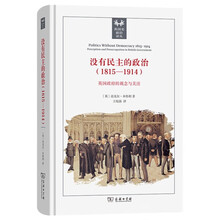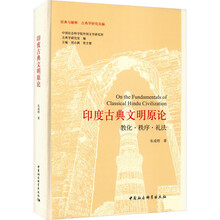最近对这种观点——埃涅阿斯的这段独白表明(如其所言)“史诗英雄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做出反驳的是斯塔尔(H. P.Stahl)。他坚称,埃涅阿斯与撒尔佩东和赫克托耳之间的联系,他的在特洛亚为狄俄墨德斯所杀的希望(以荷马为先例,以使自己提升到“最勇敢的希腊人”的水平),均积极地表明了英雄的高节,维吉尔因此得以从头就强调,“其英雄观就是荷马史诗中英雄的全面体现”。尽管如我已经表明的那样,从语境方面着眼,这里的征引最多不过是对未来事件的暗示而已,但斯塔尔却认为,对独自之肯定意义上的“重要”确认见之于它对《伊利亚特》卷二十一(即第三段引文)阿喀琉斯之类似讲辞的呼应。
为了反对奥斯汀(R.G. Austin)、威廉斯(R.D.Wlliams)和克劳森(W.Clausen)的此类观点,斯塔尔将关注点转向克劳森的评述:“对英雄,尤其是对一个正航向新世界的英雄而言,这段讲辞颇显怪异”,斯塔尔认为,这样的反应可能是因为我们对“埃涅阿斯的形象”有一个“预设(或甚至就认为是真实)”。然而,如果有这样一个预设影响了这些研究者,这个预设也不是他们,而是维吉尔给出的,是他将其安排到了史诗开篇这一可能最重要的位置上。在这里,我们和英雄相遇,他具有虔敬的美德,形象完全符合新史诗中的角色。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并未在风暴中高呼“我是此处之至伟者”(斯塔尔认为,埃涅阿斯提及狄俄墨德斯,所表达者即是此意),而是负责任地将其民族的诸神从特洛亚转移到意大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