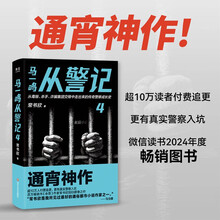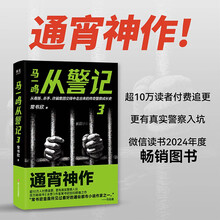吸血鬼的访客
当我们驱车准备离开时,慕尼黑阳光灿烂,四周洋溢着初夏的快乐。我们正要出发时,我所逗留的四季酒店的餐厅领班德尔布鲁克先生来到马车旁,在祝愿我一路顺风后,他握住马车门把手对车夫说:“记得在黄昏之前赶回来。虽然天看起来很亮,但已经在刮北风了,说不定会有一场风暴呢。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太晚回来的。”他笑了笑继续说,“你知道这里的夜晚什么样。”
约翰附和着:“是的,先生。”然后戴上帽子,驾着马车出发了。我们出了镇子后,我示意他停下,跳下车问:“约翰,今晚怎么安排呢?”
他一边在自己胸前画着十字一边简短地答道:“沃尔伯吉斯之夜。”然后他取下手表,那是一个老式的和萝卜一样大的德国银表,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不耐烦地耸耸肩。我意识到他这是在含蓄地向我抗议这不必要的延误,于是我又坐回了车厢,示意他继续前进。马车像离弦的箭一般飞奔上路,像是要弥补刚才耽误的时间。可就从这时起,马儿就像丢了魂一般,像是嗅到了空气中某种可疑的东西。这让我感到恐慌。当我们走过了高原,公路两旁就非常的荒芜了。前进的途中我看到了一条路,似乎很少有人走,像是在一个小而曲折的山谷里挖出来的道路。它看起来如此吸引人,我甚至不惜冒着惹恼约翰的危险叫他停下,告诉他我想走这条路。他找出了种种借口推脱,还边说边在胸前画十字。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向他提了很多问题。他巧妙地和我周旋,并不停地以看表来表示抗议。最后,我说:“得了吧,约翰,我就走这条路。你要是愿意的话就和我一起,要是不愿意呢,就请给我一个理由,我就问这么多。”他飞快地跳下了马车,这让我立即明白了他的答复。他伸出双手抓住我,哀求我不要去。还好,他的德语里夹着几个英语单词,让我大致能够猜出他的意思。有好几次他都像是打定主意要给我讲些什么——应该是某些让他忧心不已的事情;但每次他都及时刹住了车,只是画着十字对我说:“沃尔伯吉斯之夜!”
我试图与他争辩,可我们语言不通,没办法很好地交流。他显然利用了这个优势,尽管一开始就零星地说着英语单词,可他总是会忍不住地蹦出他的母语。而且每次这样做时,他都会不时地看表。马儿也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嗅着周围异样的空气。这让他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起来,惊恐地环顾了四周一眼过后,他突然跑上前,拉住马缰把它们牵到了二十英尺开外。我跟了上去,问他在干什么。他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指着我们离开的方向,那正好和其他道路形成一个十字,他先用德语然后又用英语说:“埋葬那些自杀的人吧!”
我想起人们有在十字路口埋葬自杀者的旧习俗:“啊,我知道了,自杀!真是有意思。”但我想不明白,这些马儿为何也会受到惊吓。
说话的时候,远处传来一种介于狗吠和狼嚎的声音。这让马匹显得非常不安,约翰一直都在想方设法安抚它们。他脸色苍白地说:“听起来像狼的声音,可现在这儿是没有狼的啊。”
“没有狼吗?”我问他,“以前这附近不是一直有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他说,“在春天和夏天时候是这样。但下雪的时候不会有。”
他抚摩着马儿,想让它们安静下来,乌云很快划破天际遮住了阳光,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可是一眨眼的工夫之后,太阳又出来了,而且比刚才更加灿烂。这更让人不安。约翰望着天际线脱口而出:“暴风雪来临前的宁静。”然后,他又看了看表,随后直直地走过去牵起了马缰,爬上马车,继续我们的旅途。
我觉得他还有什么没告诉我,于是没有立刻上车。
“告诉我,这条路通向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指着前方问。
他又一次在胸前画了十字,嘟哝了几句祷告后答道:“它是邪恶的。”
“什么是邪恶的?”我问。
“村庄。”
“也就是说那里有个村庄?”
“不,没有。几百年来那儿一直寥无人烟。”
这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可你刚才说有村庄。”
“曾经有过。”
“那它现在在哪里?”
于是,他用德语夹着英语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混杂的语言使我不是很清楚他在讲什么,但我大致猜得出来他是说几百年前,那儿的人死后被埋进了坟墓,却仍然可以听到地底下他们的声音,于是人们挖开坟墓,发现他们的嘴唇还是猩红的。于是人们赶紧想办法拯救他们的生命(还有他们的灵魂!说到这儿他又双手合十),村子里的人走的走,死的死,最后只剩下了——剩下了一些东西。他显然不敢说出最后这句话,继续讲下去时,他变得越来越激动,仿佛被自己的想象控制住了,说到最后他已经几近崩溃的边缘,脸色惨白,浑身冒虚汗,止不住战栗并不时地环顾四周,好像他所恐惧的那些事情即将出现在这阳光明媚的平原。最后在痛苦和绝望中他尖声叫出:“沃尔伯吉斯之夜!’并指着马车示意我赶快进去。这个时候,我的勇士血液开始作祟,我往后退了一步,说:“你害怕了,约翰,你害怕了。那你回家吧,我自己回去,我觉得散散步也不错。”我打开车门,从座位上拿起我的橡木手杖——这是我在假期短途旅行时的必备物品——然后关上门,指着慕尼黑的方向对他说:“回家吧,约翰,英国人不怕沃尔伯吉斯之夜。”
马儿此刻更是前所未有地烦躁起来,约翰设法控制它们,同时还激动地祈求我不要做傻事。我拍了拍这个可怜的家伙,他看上去如此真诚,可我却止不住发笑。他仅有的英语功底此时通通跑到了九霄云外。在万分的激动和焦虑中他忘了那唯一可以和我交流的语言工具,开始用德语喋喋不休地嚷嚷。我有些听不下去了。于是给他指了方向,说: “走吧,快回家!”然后便沿着十字路走向了山谷。
约翰无奈地掉转马车。我倚着手杖看着他朝着慕尼黑远去的背影。他先是缓缓地走了一阵,随后便碰上了一个高大瘦弱的男人。由于隔得太远,我无法看得很清楚。可是当来者靠近马的时候,它们又开始焦灼不安,并慌乱地嘶鸣起来。约翰没办法让它们安静下来,它们撒开腿像是疯了一般的朝着大路跑开了。他们渐渐地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四下里寻找刚才那位陌生人,可是他也不见了踪影。
我坐下来稍事休息,开始环顾周围的环境。此时的天气已经比我刚出来时要冷得多了,头顶还依稀盘旋着隐约的叹息声。我抬起头,看到天空中黑压压的乌云正在飞快地朝着南方行进。这应该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信号吧。我有些激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又踏上了旅途。
如今我路过的地方风景更加迷人。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吸引眼球的东西,但加在一起却显得如此和谐而惊艳。我沉浸在这一片美景之中,不知不觉竞过去了很久,直到夜色越来越深,我才猛地意识到该考虑如何找到回家的路了。白昼的光明已经隐去。夜凉如水,头顶的乌云更是让人动弹不得。远处还传来轰隆隆的响声,就像人们说的神秘的狼嚎。我犹豫了好一会儿。又想到自己说过要去看看那个荒凉的村庄,于是我上路了。不久就来到了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地域辽阔的村子。路边零星点缀着各种各样的树,小斜坡和洞穴随处可见。蜿蜒曲折的道路尽头消失在了一片浓密的树丛里。
这时,天气冷得让人发抖,下雪了。我想起此前走过的那些荒凉的地方,于是赶紧加快步伐,想要到前面的树林里寻找一个落脚之地。天色越来越暗,雪也越下越大,直到我脚下的路和四周都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条路崎岖不平、杂草丛生,我跌跌撞撞地在上面行走,脚也在杂草和青苔中越陷越深。这时风也吹得更猛了,我几乎无法迈步。空气也凝结成冰,尽管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天气,却也渐渐感到吃不消了。纷纷扬扬的大雪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天空中还不时划过一道道闪电,借着这些闪电,我看到面前有很多树,大多是紫杉和柏树,都被厚厚的雪覆盖着。
很快,我在树林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避一避的地方,那里相对安静,我能听见风刮过头顶的呜呜声。风暴的昏暗与夜色的漆黑交织在一起。不久,风暴像是停止了,只有强劲的风还残留着。周围还时不时传来狼的叫声,和某些类似的声音纠结在一起。
终于,乌云散去,月光蔓延开来,我发现自己正站在紫杉和柏树边上。雪停了,我走出去接着上路了。一路走下去,我发现了很多古老的地基,尽管如今已是废墟一片,但这儿应该曾经有过一幢房子,我还能依稀看出它的一些原形。走到灌木丛尽头时,我看到了一圈低矮的墙,顺着墙走下去,我很快就发现了出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