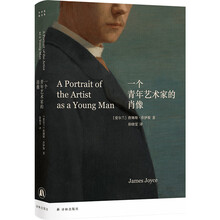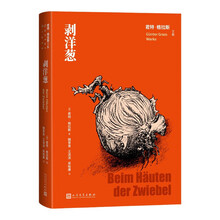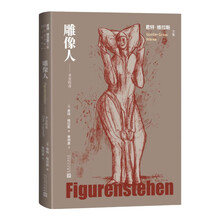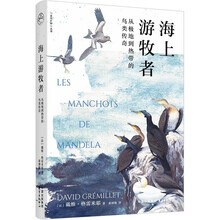1933年5月25日<br> 昨天起床的时候,脚还没着地,我就注意到了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日记本就在那抽屉里多余的床垫下面。抽屉没关好,还有白色的纸片伸在外面,像被匆忙塞回去的样子。我冲过去打开了抽屉,日记本躺在边上,没被床垫遮住。“奇怪,有人偷看过吗?”一想到有人发现了我的内心世界,发现了我的渴望与抱负,发现了我最私密的想法与感受时,我心里就冒出一股怒火。“肯定不可能有人读过!”不一会儿,热妮娅拿了个红色的小丝绸枕套进来,上面还放着一件针织套衫。“来,尼娜,这是你的吧,是吗?”<br> “是的,”我回答,不动声色地接了过来。但她一走,我就懊恼地把枕套往桌上一扔,双手抱头,大叫:“噢,畜生!猪!”枕套原本是放在最下面的抽屉里的,现在我确信不疑:一切都很清楚了。我蹲在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想起放在窗台上的多年的那把旧得发锈的钥匙。“说不定就是那把。”我拿起钥匙,试了几下,就把抽屉给锁上了。<br> 对于那个偷看我日记的人,我并不是很生气。我知道他们不会再看第二次,现在完全安全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时,又发现了另外一些蛛丝马迹,显然有人试着开抽屉,但是钥匙保护了我。我决定找出这个人是谁,到底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去问莉莉娅:“你开过我的抽屉吗?东西都被翻过了。”“东西有没有被翻过我不知道,不过我很想把它打开,你上锁了,对吗?”<br> “是的。”<br> “为什么上锁呢?我想要那个植物标本集。”<br> 我真是无话可说。<br> 热妮娅和莉莉娅还在开心地唱歌玩耍,叽叽喳喳。我的心好痛,喉咙里堵着什么。生活真可怕!有时候好想找个人诉说一切,这让我窒息的一切,我想依偎着妈妈或是姐姐们,像孩子般痛哭一场,尽情地流泪。那样儿会好受些。可我以后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生活了。<br> 要是有点儿毒药就好了。<br> <br> 1933年6月2日<br> 我现在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昨晚很早就到家了,是30号早上出发的。不会有人认为我对爸爸带我去的乡下很失望吧?噢,当然不!我还没待够呢。<br> 妈妈和我当时是坐9点的火车离开莫斯科的。车厢里人不多,火车开得慢极了,车轮滚动发出响亮痛苦的撞击声。窗外吹进一阵凉风,天色发灰,云雾低沉。火车驶过田野、森林和小村庄。铁轨的右侧密密麻麻地种着一排低矮的冷杉。墨绿色的冷杉与柔嫩新绿的合欢树小树丛奇怪地混合在一起。<br> 透过敞开的车窗,我看着摇曳的桦树、冷杉,还有偶尔出现的细长的红棕色杨树。大自然的景象真的能用语言描述吗?描述之后能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它色彩鲜明又自然的画面吗?不可能,那种触及不到也无法定义的“某种感觉”无法言喻。只有天才艺术家才能捕捉到。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目标就是描写大自然,我很努力地去做,但是……没什么进步。我已经决定用画笔代替钢笔或铅笔来描绘自然了——毕竟以前学过画画。没准毕业后还能去纺织学院的艺术系工作呢。当然了,得努力才行,但那算得了什么呢?有目标就会让生活变得轻松些,这绝对就是我要奋斗的目标。<br> <br> 1933年6月3日<br> 在交叉纵横的铁轨边走了几步我们就看到了爸爸。他慢慢地靠近我们,拄着根白色的拐杖,那佝偻憔悴的身影和胡子拉碴、晒得发黑的脸,显得他非常劳累。时间真是无情。<br> 我们三个走进了火车站旁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的牌匾上写着“大堂”与“便餐”。门口的右边,有卖报纸、杂志的。有几个人在那里排队,爸爸排在了最后面。我和妈妈走到一张桌子边,把东西放在椅子上等着。几分钟后,爸爸拿着报纸走了过来,我们就出发了。在穿过小镇后,开始沿着两旁是无尽的绿色田野和红棕色耕地的湿泥路往前走。<br> 穿过一座小桥之后,我们又走上一条湿滑的路,面前是两座石头垒砌的小平房,中间还有个半圆形的拱连着,上面好多石灰泥已经剥落,掉在这条必经的路上。我们走进院子,爬着摇晃陈旧的楼梯进了一个门廊。爸爸打开最后一扇门,我们走了进去。房间很小,天花板也很低,墙上贴着浅蓝色的墙纸。尽管空气中飘散着发霉的味道,但第一印象还真不赖。房间里充满了从小窗里照进来的让人惬意的暗光,瓶子里还插着毛绒绒的鸟樱枝和垂着的花朵。<br> 窗边的桌子上铺了白色的纸,靠墙放着一张铺着深蓝色毯子的朴素的铁床。床背后的墙边角落里,宽架子上放着些小物品。还有个样子差不多的架子靠着窗对面的墙。架子下面放着一个盖着白纸的小柜子。一堆榛木的细棍钓鱼钩躺在角落里。门的右边有一只小瓦炉。这小得可怜的房间和这些破家具看上去很脏,如果少了桌上铺的白纸,以及从那个小柜子上插着的鸟樱枝散发出来的芳香,会显得非常不讨人喜欢,而那有点儿泛蓝的柔光,多少会让所有的东西都看上去更漂亮,也更优雅些。<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