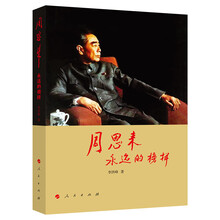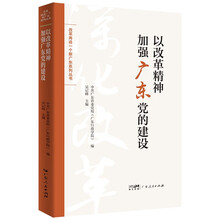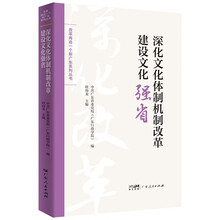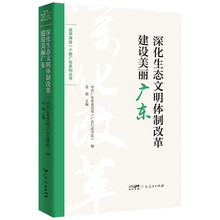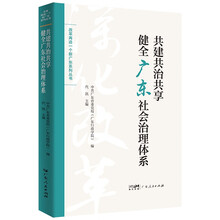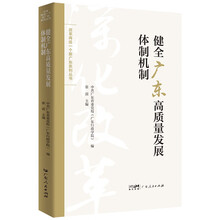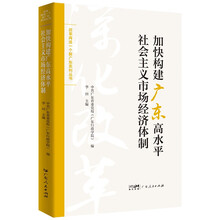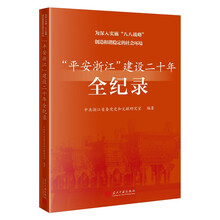,重新回到了方法论的探寻上。作为本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笔者认为中国宪法学一直是以制度研究为重心的。“以制度研究为重心的宪法学”是一种向其他法学学科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开放的学术研究取向。宪法学的研究的确需要具有学科封闭性和自足性的解释学的发展取向,这已被人们高涨的研究热情一再地证明,但也需要其他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平衡发展,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宪法学未来的研究进路也必然是、应该是多元化的:没有规范宪法学的分析基础,我们就无法精确地把握每一个宪法条款的含义,以及它在适用之时可能遭遇的各种逻辑问题;没有宪法社会学或者实用宪法学对社会经验等社会知识的引进与转化,我们就无法深刻洞悉宪法文本所依赖的这个社会环境,以及它在适用之后可能引起的社会实际后果。”周刚志:《中国宪法学如何超越“明希豪森困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01页。“以制度研究为重心的宪法学”是一种仍在持续的学术现象,但今天的制度研究比之较早前的制度研究,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受到权利本位法理学的影响,宪法学对于政治制度的描述性研究转向以权利保障为目的的反思式研究;受到法解释学的影响,制度研究重视对宪法规范进行协调性和体系性的研究,重视对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合作性研究,避免人为地割裂社会保障权与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教育权与教育法和教育制度的研究、劳动权与劳动法和劳动制度的研究等现象,因为后者往往被视做是社会法学、教育法学、劳动法学,而不是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制度研究不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理解制度,而且在制度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增强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和协调性研究。<br><br>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以制度研究为重心的宪法学”也是基于中国宪政制度实际发展的需要。在宪法解释学的发展缺乏司法实践的推动力的背景下,关注宪法中的制度安排、宪法权利的制度保障、宪法政策条款的制度化,显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实践道路。本书的研究只是这一方法论取向的初步尝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