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陆,由于其质量的庞大,使光线偏向,因此不能看到自身;使动力线偏向,因此不能遇见自身;使概念的光芒偏向,因此无法设想自身。
这样一个精神物体无疑是存在的,但它从不在我们面前出现,若出现,那是为了识别它在现实中孕育的微妙扭曲。
只有通过纯粹的类比,我们才能预感到它;只有通过纯粹的预测,我们才能依靠它。而今存在的只有紧闭的双眼,通过视网膜或者眼皮见到的只有麦角酸式的幻觉。但只需要稍稍注视这个物体,就能促使它发出额外的光芒。
这是绿光的形而上学:在白昼与黑夜之间,任何球体都可以归结为赤道上的一个点。
这是思想的绝对地平线。
所有境况都从一个物体、一个片断、一个现时的顽念中得到启发,却从来不从一个思想中获得灵感。各种思想来自四面八方,但它们被组织在客观的惊奇、物质的偏差或某个细节的周围。分析如同魔术,在无穷小的能量上耍把戏。
对于我,一个人工智慧的灵长类动物,屏幕还是屏幕。在电脑屏幕前,我搜寻着电影,找到的却只有字幕。荧屏上的文本既不是文本,也不是图像——而是一个过渡性的物体(视频就是一个过渡图像),只有将它从一个屏幕折射到另一个屏幕,变成互不连接的光谱信号时,才具有意义。
在思考邪恶问题时,最难办的就是将任何不幸和犯罪感的概念从思想中清除出去。
是否应该真的强迫自己去思考?有时会觉得,另外一种经历,即思考和写作动力逐渐衰退的经历,或许会更加清新,更加奇妙。那么这种习惯的改变究竟能到什么地步?
任何宿命都位于相互无关紧要的进程的交汇处,因而相遇(包括爱情缘分)的概率微乎其微。但这种最小的概率也夹带着一种预料,以神奇的速度增加着相遇的机会。宿命就像一个镜子游戏,自我安置在这种微弱概率和这个绝对预感的交汇处。
要为理论的曲解或误会辩护是没有希望的,就像这个黄油面包片的故事:萨拉来见犹太教主持,对他说:“啊,真是一个奇迹!今天早上,我的面包片掉在地上,可涂有黄油的一面并没有朝下!”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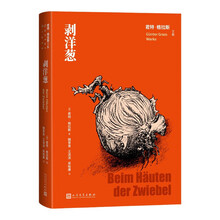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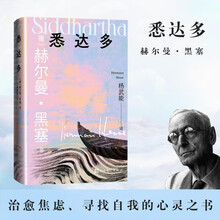

——Susan Willis, Duke University
犀利,阴郁,才气卓然,具有爆发力,这些碎片都有各自所针对的目标:我们的技术理性的优越感与胜利进程的基本预设——以及我们“当前各种形态的绝望”。
——Mike Gane, Loughborough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