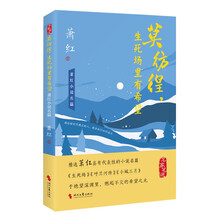车前子的美食
张季鹰的莼菜
车前子说:“在澄澈的月光下,我想起莼菜了,张季鹰的莼菜。”(《明月前身》)莼菜,草字头底下一个纯字,纯净的纯,也是纯粹的纯,如此纯粹纯净之物应该在月光下食用——月光像雾,莼菜也像雾。
莼菜在中国历史上了不得,在中国文人眼里更是不得了,一个叫张季鹰的男人放弃高官,就为了回家吃莼菜,把二十四史上的大小官僚惊呆了——张季鹰这个名字好,有魏晋风骨,为了莼菜,他把多少人钻山打洞想得到的官帽子抓起来朝地上狠狠一扔,说不定还踹上几脚,拍拍屁股就回家吃鲈鱼与莼菜——拿现在的话说,张老头真是帅呆了酷毙了,与陶渊明陶老头有得一拼。很多人不可能做到张季鹰那样的洒脱,但是莼菜还是想尝一尝,它到底是何样的滋味,让一个人心甘情愿把官都丢了?万贯家产妻妾成群全丢了,就为了这一碗莼菜汤,这人脑子进水了?或者像电脑一样感染了蠕虫病毒?
车前子说:“莼菜的确好吃。纯粹。一般做汤。我曾吃过莼炒鱼脑,恶俗。自创过凉菜一道:莼拌银耳。稍嫌生硬,但也不失清味。”老车在这里有点人云亦云,说莼菜好吃是因为纯粹。纯粹作何解?又说莼拌银耳不失清味,这一点也难以站得住脚,张季鹰为了它把官都丢了,难道就是为了似是而非的清味与纯粹?我认定张季鹰拿莼菜说事只是找一个借口,可能他嫌理由不足,还搭上一条松江鲈鱼——他其实早就厌倦了为官钻营之道,或者他根本就是个无能之辈,早有归隐之心,于是就人为地制造了一个莼鲈之思,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炒作。莼菜在我老家土名杏子叶,池塘里多的是,是用来喂猪的,请原谅我这样暴殄天物——家里猪饿得嗷嗷叫了,农民拿两根竹竿到池塘边,夹住杏子叶细细长长的藤,朝一个方向绞动,很快就绞了满满一竹竿,背回家来喂猪。但是杏子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张季鹰所说的莼菜,莼菜其实是杏子叶没出水的嫩芽,它上面包裹着一层黏稠的液体,黏液像一团雾包裹着叶芽,准确说,张季鹰在洛阳的梦想之物,便是这个叶芽。北方武将不懂莼菜为何物,被张季鹰唬得一愣一愣的,其实也没啥——我亲手摘来做过汤,用汤匙舀了半天也舀不起来,最后只得捧起汤碗往嘴里倒。还是车前子描写得最准确:“满满的莼菜呀就被收拾到调羹里,调羹捕莼,焉知乌嘴在后,浅浅急急捞捞舀舀,往往擦肩而过。因为莼菜腻滑、幻华,思之容易,吃时难矣。”——可是即便吃到嘴里又能怎样?就是一股清味,叶芽还微微发苦,农民对它有一个更贴切的绰号:草鼻涕。
江南风雅之士就喜欢搞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头,油炸豆腐叫做金镶白玉板,小菠菜叫红嘴绿鹦哥,连最烂贱的黄豆芽也叫什么金头玉如意,把草鼻涕炒作成莼菜,张季鹰堪比大嘴巴宋祖德。不过这个叫季鹰的男人倒是真的由此开始大红大紫,古往今来的文人雅士,谁没有抬头看过这只季节的鹰啊?他从西晋飞来,朝宋元飞去,嘴巴里死死衔着一棵莼菜——
田家屯的韭菜花
车前子喜欢韭菜,喜欢杨凝式的《韭花帖》和长春九台的韭菜花——《韭花帖》与韭菜花其实密不可分,杨凝式的《韭花帖》正是源自春天的韭菜花。
好像诗人很容易就爱上韭菜,杜甫一首“夜雨剪春韭”,让韭菜在唐诗里扎下了根。韭菜只要留着那一点根,就可以一茬接一茬地生长,一茬接一茬地开花。韭菜花清白洁净,像杜甫的句子“夜雨剪春韭”,最是清白洁净,一种诗歌的清香——这是食草动物独有的悲悯。车前子这样说:“一到春天,吃也绿油油了,最绿的是韭菜……”(《春天的吃》)所以,车前子连带着也喜欢上杨凝式的《韭花帖》。杨凝式这个人怎么说好呢,他就像一丛韭菜,开花的韭菜生长在古代的田园——他多半是一个过渡人物,夹在唐代颜柳欧褚和宋代苏黄米蔡之间。他的《韭花帖》是一个偶然,偶然的也就是必然的。据我看来,那应该也是一个春雨如丝的夜晚,朋友路过杨凝式家,顺路带了一把韭菜花送他。可能是韭菜花在菜园里在春雨里开疯了,朋友喜欢,认为杨凝式必定也喜欢,就采了一把送他。雨水湿透的韭菜花果然让杨凝式爱不释手,他一半清供于案,另一半就搭配着羊肉一块吃了,韭菜花的香气掩盖了羊肉腥膻味,这春夜的美食,味道自然好得没法说。杨凝式一时兴奋坐不住,当即研墨给送韭菜花的朋友写了几行字,“当一叶报秋之际,乃韭花逞昧之始”,好像报秋不对,韭菜分明春天开花,也许北方韭菜开花迟一些。反正就是这一纸便笺,成了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韭花帖》——《韭花帖》风行于书法圈,韭菜花配羊肉也风靡于美食界,吃羊肉如果少了韭菜花,就如同在重庆吃火锅没有辣椒,就如同在北京吃烤鸭少了大酱——连汪曾祺也这样说:“北京现在吃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或以为这办法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原来中国五代时已经有了。”杨凝式正是五代人,无论是《韭花帖》还是韭菜花,都是五代人杨凝式开了一个好头。
车前子在长春九台住过两个月,那里的韭菜花让他一食难忘,他最爱杨凝式的《韭花帖》,大概也与这段乡居生活有关。九台在长春,那里家家都有一个石臼窝,就是用来腌韭菜花的,将含苞待放或花开半朵的韭花花穗剪下来,在石曰窝里一下一下捣烂,一定少不了生姜与辣椒,当然还有盐,并且盐一定要多放。车前子说:“田家屯的韭菜花够咸的,也够新鲜,腌得时间不短,但记忆里依旧翠绿。”韭菜花一定要咸,这样它才能保持翠绿的颜色,如果淡得发酸,那是不能上台面的。我的习惯不是用羊肉蘸韭菜花,而是用韭菜花蒸臭豆腐,这是奇特的美味,适合于车前子或汪曾祺的口味——我是典型的江南人,不太能接受杨凝式的韭菜花配羊肉,所以——我永远也写不出《韭花帖》。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