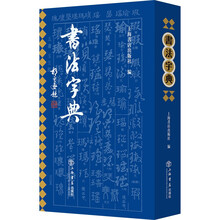住院随笔
我住进浙二“六一六”病房的准确时间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十五时五十四分。
我站在“护理站”门口时,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女护士正拿着一张表格在对另一位护士说:“这个‘苇白,怎么不来了?”我赶紧凑上去说:“曹操到了。”
床位好极了,是靠近阳台临窗边的,朝外看,有屋顶,有天线塔,有高吊车,还有一排淡黑的山。
护士通知我,因为我来得太晚,晚餐无法供应。我只好外出设法填饱肚子,正是下班时刻,行人匆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这儿离官巷口不远,我想起了“奎元馆”,想起了那著名的“片儿川”。解放前,我第一次来到省城,就曾慕名来过。“大东阳火腿公司”栈房里的年轻伙计调排我,说杭州人讲话都带“儿”,那面条不叫“片儿川”,要叫“片川儿”。就这样,“奎元馆”的跑堂大吃一惊,来了个要吃两碗“片川儿”的乡下小伙子。那味道,至今回想起来仍是美不可言,现在,又勾引我朝此馆走去。但当我吃着“正宗”的时候,却觉得不怎么样。其一,两元一碗的面,味道确实只是一般;其二,和我同桌子的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个像我的外孙女一般大的小孩吃的是十八元一碗的面条。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我不糊涂,清楚记得自己是有四十年教龄的老教师。
还是那歌词全面,另有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纳米“匹夫”
梅季一过,酷暑的味道就一天比一天浓了。不过,早晨还是挺凉快的,尤其是从断桥骑自行车冲下去那一刻,惬意没得说。
正享受着,耳听得有人叫我:“苇老师!”
赶紧刹车,回头一看,老赵的夫人正笑着站在一边。
“赵夫人好,怎么这么早就往回走了?”
“走了一圈,得回去了,家里事多着呢。”停了一会儿,夫人像是有点怨气,“现在的老赵不听话了。本来么,还帮我晒晒衣服、抹抹桌子什么的,可现在,现在他什么都不管了。
这老赵,是我在“孤山一片云”喝早茶的晨友、茶友,现在又是做明信片的“战友”了。你别看他离休前在单位里是什么什么的,可在家里就成了小卒卒了。夫人支配他,自不用说,儿子、女儿也随时可以“抓壮丁”,就连八岁的外孙也常常爬到头上去,随便吆喝。而老赵总是有求必应,脾气好得如同弥勒佛。
“什么都不管了?”我笑了,“不会吧。”
“他呀,自从开始做明信片,就一门心思‘新概念’了。叫他吃饭也不理,常常过了十二点等他做好了才吃,菜都凉了,你说气不气?”
“气、气。”
“还有呀,你不知道,有天夜里他一直做到将近十二点了。这‘丑老鸭’废寝忘食都快成精了。
赵夫人说归说,却笑着。我不知道她是在表扬老赵呢,还是心疼老赵,只是她吐露的,我绝对相信。“由来同一梦,世人休笑痴”,成熟的男人,都有事业心、执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