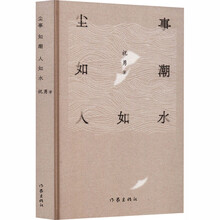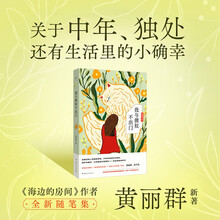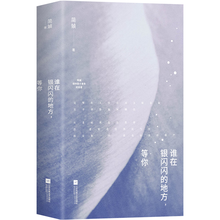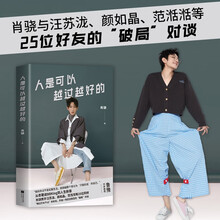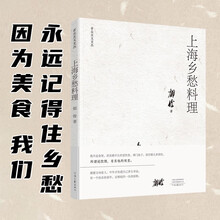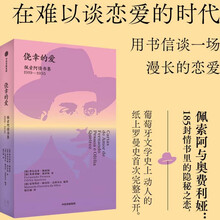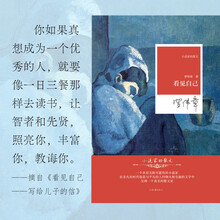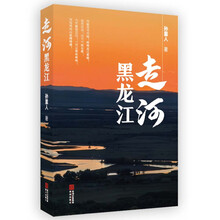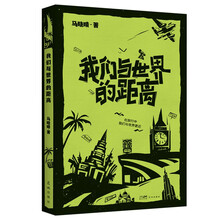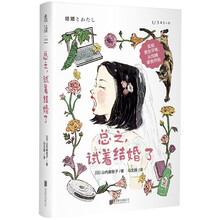谁也没有办法否认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民心。情是这样的情,理是这样的理,激愤、期待,也充满信任。无怪乎据说一些老解放区的歌唱家聚会的时候,在酒过三巡以后,他们宣告:革命的胜利是从他们的唱歌儿的胜利上开始的。
我想起1949至1950年苏联协助拍摄的文献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解放了的中国》,后一部影片解说词执笔人中方是刘白羽,苏方是西蒙诺夫。
也许你可以追溯到蒋介石的1927年的“四一二”血洗,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秋瑾与黄花岗烈士的就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窦娥冤、秦香莲、杜十娘直到黛玉、晴雯、鸳鸯、金钏……也许还应该提到《兰花花》与《森吉德玛》,应该提到遍布神州的节烈牌坊与牌坊下的冤魂厉鬼。风暴与渴望孕育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点点滴滴、零零星星、血血泪泪,终于汇聚成了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的狂风暴雨。只有不可救药的白痴,才在全面小康着的中国冷言冷语:“有那个必要吗?”“代价太大了啊。”“如果没有这一切,一直搞建设多好!”
民歌的力量
旧中国城市里的流行歌曲,尽管也颇有可取,如《马路天使》、《渔光曲》里的插曲,但同时也确实与旧社会一起透露出了土崩瓦解、鬼哭狼嚎、阴阳怪气的征候。例如1948年流行的《夫妻相骂》,女骂男:“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也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男骂女:“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邻居骂:“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
而解放区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太阳出来了,满呀嘛满山红”,“东北风啊,刮呀,刮呀,刮晴了天啊,晴了天,庄家人翻身啦……”
我始终认为这最后一首东北民歌,是土改歌曲,饱含着感情,也饱含着斗争的严酷。它使我一唱就想起周立波的获得斯大林奖的作品《暴风骤雨》。当然,有的人读了周立波的小说会浑身寒战。正是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使千千万赤贫的农民走上了革命到底的义无反顾之路。正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全面革命化,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成为中国革命必胜的保证。
“庄家人翻身啦”一句,离开了旋律调性,它是呼喊,是叫嚷,是霹雳电闪,它唤醒了阶级,带着拼却一身热血的决绝。
与旧的流行歌曲相比较,民歌风更刚健也更明快,更上口也更泼辣。五十年代的我们,认定是共产党带来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与蒙古长调,还有四川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早在解放前,是地下党接收了推广了并非共产党人的教授老志诚所整理的新疆民歌《阿拉木汗》、《喀什噶尔姑娘》,使之成为平津学生大联欢的主唱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贡献是开掘了、辑录了也充分使用了如此丰赡的民歌民谣,开掘弘扬了我们的民族民问精神资源。
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新疆缘分。在解放头两年的众多的欢庆解放的歌曲里,一首新疆歌儿令我如醉如痴:
哎,我们尽情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
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
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泽东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温暖……
你觉得这歌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心底的深处、含着泪、又破涕为笑了才唱出来的。人民,只有人民,让我们永远记住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期望和贡献。
这样的歌词与真情千金难换。
老式的唱片上,一面是此首歌,另一面是器乐合奏《十二木卡姆》的一个片段。十二木卡姆也是随着解放才兴旺发达起来的。
1951年,我从一张纸上学会了我此生的第一首维吾尔语歌曲,这张纸抄写了用汉语记录的维吾尔语发音的歌词:
巴哈米兹能巴哈班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伟大的毛泽东)
阿雅脱米兹能甲尼甲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伟大的毛泽东)
无论如何,这样的歌词是太可爱了,别具一格。次年,苏联艺术家访华演出,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塔玛拉·哈侬演唱了它,最后一句歌词是一串笑声:啊哈哈哈……她笑得十分出彩。与她笑得一样好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哈丽玛·纳赛罗娃唱《哈萨克圆舞曲》。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