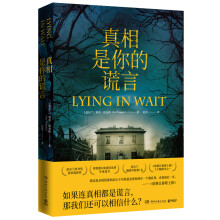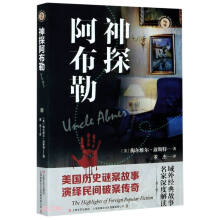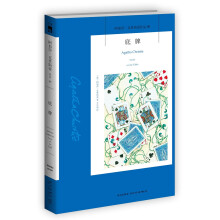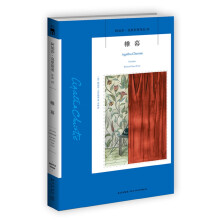机关舞会
她到这个机关工作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可是她打着两根小辫,粗乱的眉毛,斜背背包的模样却像个大学刚毕业的女生。在那个年代,读大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她没有机会。可她的运气还算不错,进了这个国家机关工作。
这个机关坐落在上海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上,里面都是一些戴着袖套工作的知识分子,见人喜欢谦虚地弯腰致意,文质彬彬。她有些羞涩,自己并不是知识分子。她被分配到机关的办公室做事。办公室有一屋子的人,每个人有一个办公桌,玻璃台板下夹着一张当年的年历。
她戴上一个自己用缝纫机踩的蓝底碎花布袖套,和大家一样,埋头处理文件、资料,抄写,编制页码和目录。上班的时候,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偷眼望去,似乎人人都低眉顺眼。可是有一天,颧骨高高的主任很突兀地说道:“有些小青年要学习是好事,但是上班时间要遵守劳动纪律。”
她就听见右边角落里,铁皮抽屉哗啦一声合上,一个男青年抬起头来朝天花板“呵呵”笑笑,他长得十分白皙,五宫凹凸分明,脖子很长,侧面看上去有点像画素描用的石膏像。接着他打了一个很大的哈欠,远远看过去,他的眼珠上似乎有些血丝。
“怎么样?”主任的口气忽然又软下来,慈祥地说:“年纪轻,晚上也不能睡得太晚,先用冷水毛巾去擦一把脸,等会吃了午饭,把席子摊开补一觉。”话音一落,他就笑嘻嘻地站了起来,他笑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大,露出的牙齿有烟熏的痕迹。他从椅子背后抽下一块颜色模糊的毛巾,摇晃着肩膀走出来。
办公桌横排成一长条,每个桌子间留了很少的缝隙,只有她这边,因为新放好桌子,尚未匀给人家尺寸的关系,有一条比较大的过道。他摇晃着肩膀走过来,嘴里哼着一支不明的曲子。前几天主任把她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他不在,所以她不知道,办公室里除了一个胖子之外,还有和她年龄相仿的同事。她感觉到他走过来,并且感觉到他的直视,心里一阵慌乱。
他从过道中挤过去的时候,对着她低下的头皮似乎哈了一口气,并轻轻打了个响指。她的睑瞬时红了,些微的愤怒窜上喉咙,她是一个有些泼辣的姑娘,公车上、夜路中遇见轻浮男人的时候,她不是吃素的。可是在这间办公室,她还是新来的,她忍了下来,没有抬头。
她是一个心思很简单的女人,不关心自己长得美不美,她不会打扮,也不化妆。她有一头乌黑顺滑的头发,额头发角都有些蜷曲,所以她也从不烫发,简单地用黑色松紧圈松松地在脑后扣一条马尾。她的衣服有很多都是嫂嫂穿下来的,她嫂嫂喜欢打扮,还有一个海外的亲戚常常捎来衣服。
才来了没几天,她的穿着便给人留下了印象。中午去食堂吃完饭,她拿着搪瓷碗回来,在大门口,机关里一个老同志停住脚步望着她,抑扬顿挫评论道,昨天你是牧羊女,今天怎么变成了公主?她穿了件蕾丝花边的长衬衫,有点像短裙子。“真的吗?”她顽皮地将衣服边张开,做了个屈膝的动作。老男人和她开玩笑她不生气的,老男人在她的眼中似乎是没有性别的,打个情骂个俏只仿佛锻炼口才,她也不小了,隐隐的刺激她能够承受。
这时,他从她身边擦过去,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弓了弓腰,很一本正经地对着老同志叫了一声老师好。她的脸又红了,所幸他似乎没有注意到。
回到办公室,还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有的女同事到隔壁房间打毛线聊天去了,有的出去逛街买东西。她的椅子背后有一卷草席,是主任叫她去领来午睡用的。办公室地板是打蜡的,细条木板,很干净,将椅子移开,那距离铺一张草席刚刚好。可是,她没有午睡的习惯,便拿了本小说杂志,准备打发这段时间。
她的眼睛不敢东张西望,因为她感觉到办公室的几个角落已经躺下了不下三四人,尽管大家都和衣躺着,有的还在小肚子上搭条毛巾,然而毕竟人家玉体横陈不设防,瞄到一眼心里也蛮“罪过”的。
她缩小视野,像患了青光眼的人一样,视线成锥型,不给侧光和余渡,专看眼前十六开大小的杂志。天很热,人声静下来,窗外蝉鸣有一搭没一搭,老式吊扇“壳隆隆”有规律地轰鸣。渐渐地,办公室充满了夏目的疲倦,她的脑袋不由也耷拉下来,索性弃了书,伏在手臂上睡着了。
她跌倒在手臂上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角度的问题,于是,她面向着北,左脸颊压在粉白的手臂上,睫毛似小扇子盖在眼上一跳一跳,鲜红的嘴唇微微启着,有一丝涎水爬下来。惊觉到有射线偷看她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有七分醒了,可是还有三分是糊涂的,她怔怔地看着那条射线的来处,一张似笑非笑的脸隐约晃动。
“啪嗒……”目光灯打开,上班的时间到了,有人开始重手重脚做事情,高声谈笑。她猛然坐直身子,想不到自己竟然睡着了,她不好意思地取出小手帕,擦掉嘴边有点腥味的诞水。
北边角落里,他从地上爬起来,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咯啦啦”的响声,仿佛很观乐雀跃。她皱紧了眉头很后晦,被人偷看去的睡样,一定是很丑的。
他来到中央,将燃着的烟叼在嘴角,两只手臂抬起来,一只高些,一只低些,无形中 像是端着个什么蛮大的东西,忽然地他就转起圈子来。嘭嚓嚓,嘭嚓嚓,他嘴巴含含 糊糊数着三步舞拍子
还是夏天。黄梅季节到了,连着下几天雨后,人都有一种孤独感,心里面潮乎乎的,希冀升起又破灭,仿佛没有盼头。
每天下午三点钟,机关里是要做广播操的,可是天下着雨,没有人愿意出去。几个同事伏案久了,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走到门外。这幢洋房的旧主人很有来历,走廊的顶有三人高,廊柱是西班牙雕塑式的,落地铺就的大理石每一块都有很优雅的金线嵌条,整条走廊开阔,却有一股逼仄的威严在里头。
他在人群中吸烟。他吸烟的样子很迷人,让她想起自己向父亲。她向父亲也是吸烟的,瘾很大,一天两包,别人吸烟身上很臭,可是她父亲是香的。她父亲已经死了很久了,可是老头儿身上那股令人迷醉的香味她还记得。
他的手指长而白皙,夹住小白棍的时候微微有些颤抖,神经质的。嘴唇凑上去吻住烟的一瞬间,她看见他的眼睛中总是有泪水似向东西漫过来。不知道为什么,每当这种时候,她的心会痛一下。这是一个艺术型的男人,她想,易感的男人。
他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围着一起吸烟的男人都笑起来,有人向后退了一步,让出一块空地。他来到中央,将燃着的烟叼在嘴角,两只手臂抬起来,一只高些,一只低些,无形中像是端着个什么蛮大的东西,忽然地他就转起圈子来。嘭嚓嚓,嘭嚓嚓,他嘴巴含含糊糊数着三步舞拍子。哈哈,哈哈哈……大伙都憋不住笑了,有人把头别开,好像怕打断他的兴致。她虽然站在远处,看到他在大庭广众下跳交谊舞,在众人的嘲笑或是哄笑中像陀螺似的停不下来,也感到很尴尬,关我什么事情呢?她镇定下来,带着些微怒气回到办公桌前。
后来他又在走廊里表演过几次,围观的同事也越来越多,楼上楼下大家都知道他会跳舞了。偶尔的,也有一两个不甘寂寞的老师闻讯过来,非常晾喜于交谊舞的复活,忍不住摆一两个动作,显显身手。一天,人事科的副科长办事路过看见,同事一哄而散,副科长拉住他,半嗔怪地说:“你要死哕,我告诉你爸爸去。”他嬉皮笑脸:“我又没做啥,跳舞算啥啦,改革开放了,思想开放点嘛。”
她这才想到,他那奇怪的姓氏和局机关领导是一样的,当真是干部子弟,果然不同凡响。她心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的父母是一般的职员,一切都要靠自己的。业余时间她一直在夜校读书,清心寡欲,虽然不知道学了以后在机关能否派到用场。努力总归是对的,她工作也很卖力。
跳交谊舞的风终于刮到机关里来了。机关大厅里由工会出面贴出一张海报,周末在大会议室举行迎国庆舞会。那一个星期里,整幢机关楼仿佛被点燃一样,有人从家里带来四喇叭的收录机,中午和下午广播体操时间都有人聚拢来研究舞步。一个从部队文工团复员回来的老张成了老师,他跳舞的步子出奇的大,两只手将舞伴抓住,展开人家的臂膀,仿佛鲲鹏展翅。一个资产阶级老小姐似的老师努着嘴巴很不以为然,她偷偷地在自己办公室跳给人看那种优雅的舞步。
她的好奇心渐渐被激活了,克服了先前的忸怩,闪着亮晶晶的眼眸靠在门框上看大家踩步子。他们这个科室有十几个人,中年以下的几乎都不会跳舞。老张满头大汗,教了一个又一个,她也被抓到,一二一二地教她最基本的慢四步布鲁斯。她的脸涨到通红,常常忘记老张的叮咛,要把头低下去看那双脚。其实她看脚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她要透气,老张嘴巴太臭了,烘烘地蒸腾出来的气体简直要把她熏死了。
她身材窈窕,有胸有屁股,也不算笨,小时候体育课上经常做领操的,跳起舞来胳膊、腿都摆得挺有架势,但是她的耳朵不行,对音乐不敏感,怎么也分不清节奏。音乐一响,那个老张就要考验她的听力:“三步还是四步?”她的脑袋立马“轰”地一下炸了,她听不出来,只好傻笑,被老张拉扯着移动。这样,她脚步、身子总体上像一根木头,一板一眼很没有韵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