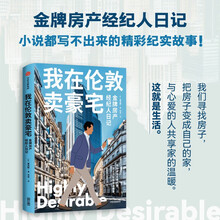岳维峻是国民党整编三十四师师长,蒋介石的亲信。他的臭名所以能传遍大别山地区,倒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是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第一次反围攻中被活捉的一个师长。
一九三○年,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革命的火焰在大别山区熊熊地燃烧起来,震撼了国民党的腑脏——南京和武汉。年底,蒋介石怀着恐惧和仇恨,挥兵向鄂豫皖红军“围剿”来了。经过根据地军民给敌以严重的打击后,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旬,敌人向我反扑,前线指挥官就是岳维峻。为了“欢迎”他,鄂豫皖根据地军民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活捉岳维峻!”这口号表达了全体军民对这次反“围剿”的意志和决心。
消息传来,岳维峻已到达孝感县的双桥镇。我们准备趁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把他吃掉。第二天中午,部队到达离双桥镇五十里的一个小村子。吃了午饭,大家一面擦拭武器,一面谈笑着:
“班长,岳维峻长得怎么个模样?”
“不知道模样,怎么逮昵?”
我只是笑了笑。岳维峻长得什么模样,鬼才知道;反正是两只眼睛一张嘴,绝不会有三条胳膊四条腿吧。
正在说笑,连长王泽先同志来了。我急忙站起来,心里猜想:十有八九是来了任务了。果然不出所料,我们班被任命为尖兵班,天一黑就出发。
我心里乐得不得了。瞅瞅大伙,也都是眉飞色舞的。等连长一走,大家相互搂抱着,用拳头捶着对方的胸脯,快活得大声呼叫起来:
“今晚上就把岳维峻逮过来!”
“我要亲手把他绑起来!”
可是,活捉岳维峻真像说的那么轻巧么?
天黑,部队出发了。在潘塘附近,我们捉住了一个敌人的潜伏哨。刺刀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他就详详细细地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了我们,并说前面庄里还驻着一个连。
连长刚好走来,他听完我们的汇报,沉思了一下,向我低声叮咛了几句。我转过身来,厉声向俘虏说:
“老老实实带我们到前面庄子里去,叫你怎么干就怎么干!”
“是,是,当然,那当然……”他连连点头。
走下山坡,来到庄子前。黑糊糊的一棵大树后突然传出:“口令?”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
我连忙用手捣捣走在我们中间的俘虏。他马上回答道:“战!”
哨兵从树背后走出来,还没有停步,刘汉祖抢上两步,把他拦腰一抱,摔倒在地上;俞先润扑上去,把一块擦枪布狠狠地塞进了那张正想叫唤的嘴巴里。
冲进庄子,俘虏带我们到了一所茅屋前。踢开门,屋子里黑沉沉的,光听得地上响着一片猪一样的鼾声。一个战士用手电筒往里一照,我们就顺着这道亮光向里猛打了一阵排子枪。敌人被打得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号叫起来:“我缴枪,我缴枪!”
这时,我们营已全部冲进了庄子,彻底解决了敌人的前哨连。从俘虏的连长身上,搜出一份用复写纸画的地图,上面详细地标示着敌人的兵力布置。这是一份重要文件。我急忙去找连长,迎面正碰着团长周维炯同志。
周团长就地坐了下来,用手电筒照着地图,问那个被俘的连长:
“岳维峻的指挥部在哪里?”
“就,就在这座房子里。”被俘的连长用发抖的手指着双桥镇北面靠河边的一个小屋。我站在旁边看着地图,努力记住:北面——靠河边——独立小屋。
部队接着以连为单位,向双桥镇挺进。不管是大路还是小道,不管是田埂还是水沟,只要踩得住脚,我们就一股劲地向前跑。四周寂静乌黑,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咳嗽,只听得急促的脚步声。
走着走着,天亮了。大雾向山壁靠去,渐渐地变成了缠在山腰上的飘带。这时,我们才看清前面有一座长五六里、高百来尺的山岭,山半腰修筑着敌人的一道集团工事。
雾还没有散尽。这是进攻的好机会。周团长立即命令我们行动。
我们接近到集团工事旁边,敌人的哨兵还在悠闲地哼着下流的小调。我们甩去几十个手榴弹,尖声细气的小调,一变而为没命的号哭。没等工事里的敌人还手,我们的一、二连从正面攻上来,三营又在他们右背后打响了。
敌团长被打得晕头转向,摸不清来了多少红军。就不顾一切地往南山逃。哪知道我们二营正好在南山坡。迎头一打,活捉了敌团长。消息传来,我们就向工事里的敌人喊道:
“你们的团长被活捉了,缴枪吧!”
一个团就这样解决了。下一步棋就是攻打双桥镇,活捉岳维峻。
但事情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容易。敌人失去了阵地,以两个团的兵力,从我们的两侧反击上来。炮火不断地向我们轰击,山头上硝烟弥漫。我们凭着夺得的工事,以手榴弹抗击敌人。正酣战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忽然接到撤退的命令,原因是二营阵地已被敌人重占,我们三营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我们并没有放弃活捉岳维峻的决心。部队休息了一阵,重新组织冲击。这时,敌人不仅居高临下用机枪向我们扫射,还从武汉方面飞来三架飞机助威。炮弹和子弹,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辛辣的火药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身子贴伏在地上,利用敌人射击的间隙,向前跃进。到了距敌人工事一百米远近时,猛然跃起,冲上去跟敌人拼刺刀。
一场恶斗开始了,刺刀与刺刀相碰的声音,夹杂着敌人的惨叫声。刘汉祖正向一个冲来的敌人刺去,那个敌人拨开他的枪刺,顺势一下,戳到他的头部。刘汉祖扑通一声跌翻了。我的心紧缩得像要跳出来似的,用尽全身气力,把敌人刺了个腹背对穿……
这一次攻击,终因我方伤亡过大没有得利。部队又奉命撤下来。
太阳正当头顶,炊事员早已把大米饭和猪肉挑来了,可是大家都气得不想吃。我检查一下班里的同志,剩下一半了,心里更是难过。
饭后,各班排合并的合并,补充的补充,连炊事员陈兆明也编到班里当战士了。
战斗的空隙里,敌人还稀稀落落地向我们放炮。周团长站在田埂上,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空中响起一串刺耳的声音,我们都急得高声大喊:“炮弹来了,团长!”话未落音,只听得“咣!”一发山炮弹在离团长不远处爆炸了,尘土飞扬起来,溅了团长一身。我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可他只是抖了抖身上的灰土,又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敌情——我们的团长正在为着组织第三次攻击而费脑筋哩!
这时,从双桥镇东南方向,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周团长忙跨上高坡观察,很快转过身子来,挥动着手臂,大声说:
“快组织进攻!三十一团已截断了敌人后路。”
听说三十一团在南面打响了,我们都霍地站起来。已经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捉不住岳维峻,怎能消心头之恨呢?攻击部队分成几个箭头,准备停当,听团长一声喊:“冲啊!”部队又向上攻去。
这一回,我们前后夹击,打得敌人顾头不顾尾,火力部署也被打乱了。我们一股劲地冲上去,将敌人冲得四散奔逃。我们重新占领了敌人的阵地。从山上往双桥镇望去,只见西边的土山顶上,也插了红旗;镇上的敌人,正沿着大路,往孝感县方向逃命。
周团长从后面赶上前来,拿起望远镜一看,连连跺脚说:
“坏啦,岳维峻要溜!同志们快冲下去抓呀!”
一刹那间,我们像雪崩似的往山下拥去。来不及逃掉的敌人,慌忙把枪举在头顶上,跪下来。我们谁也没空去理他们,追啊,追啊,直奔河边的独立小屋。谁知道冲进屋子一看,里面空空的。我们又连忙从屋里追出来。往前望去,只见大路上有顶四个兵抬的大轿子。
“岳维峻,岳维峻!”一个同志指着轿子大叫起来。我们拔起腿又追,一面跑,一面喊:
“抓活的!抓活的啊!”
离轿子只有几百米远了,我们对空放了几枪,威胁抬轿的敌兵:“站住!不然就打死你们!”
他们一回头,腿都吓软了。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轿子包围住,可是往里一瞅,哪有什么岳维峻,连个人影也没有。又被这个兔崽子骗了!我们气得把轿子捣了个稀巴烂。
“快说,岳维峻逃到哪儿去了?”
“大……大概在前面!”那几个抬轿子的现出一副可怜相。本来嘛,他们也都是受苦人,我们就不再难为他们了,只叫他们讲讲岳维峻什么模样。
“高高个,胖胖的,鼻子下面有撮胡子……”他们比画了一阵子,我们等不及听完,又往前追去。
追了很多路,见前面河边围了一大堆人。哎哟!这一定是被别人占了先啦!我们急急地跑过去,挤进人堆一看:可不是,正中间站着一个穿蓝色绸长衫的老头,腰粗得像个汽油桶,那颗脑袋活像一个刮光了毛的肥猪头,大约是逃得太累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呼哧呼哧喘不过气来。这老头,就是岳维峻。
战斗胜利结束了。岳维峻被押着离开了战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