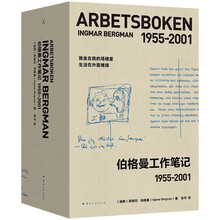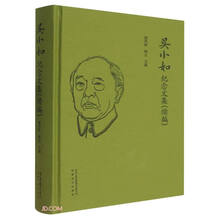今年二月间,我们进了北京。这城市,我也是第一次来,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虽然我离开大城市已经有十二年的岁月,虽然我身上还是披着满是尘土的粗布棉衣……可是我暗暗地想:新的生活开始了!
可是她呢?进城以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深山、大沟和沙滩;这城市的一切,对于她,我敢说,连做梦也没梦见过的!应该比我更兴奋才对,可是,她不!
进城的第二天,我们从街上回来,我问她:“你看这城市好不好?”她大不为然,却发了一通议论:那么多的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头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得!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血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得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嚷嚷,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说到最后,她问我:“他们干活不?哪来那么多的钱?”
我说:“这就叫做城市呵!你这农村脑瓜吃不开啦!”她却不服气:“鸡巴!你没看见?刚才一个蹬三轮的小孩,至多不过十三四,瘦得像只猴儿,却拖着一个气儿吹起来似的大胖子——足有一百八十斤!坐在车里,跷了个二郎腿,含了支烟卷儿,亏他还那样‘得’!(得意;自得其乐的意思)……俺老根据地哪见过这!得好好儿改造一下子!”
我说:“当然要改造!可是得慢慢地来;而且也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
她却更不服气了:“嘿!我早看透了!像你那脑瓜,别叫人家把你改造了!还说哩!”
我觉得她的感觉确实要比我锐利得多,但我总以为她也是说说罢了,谁知道她不仅那么说;她在行动上也显得和城市的一切生活习惯不合拍!虽然也都是在一些小地方。
那时候,机关里还没起伙,每天给每人发一百块钱,到外边去买来吃。有一次,我们俩到了一家饭铺里,走到楼上,坐下了。她开口就先问价钱:“你们的炒饼多少钱一盘?”“面条呢?”“馍馍呢?”……她一听那跑堂的一报价钱,就把我一拉,没等我站起来,她就在头里走下楼去。弄得那跑堂的莫名其妙,睁大了眼睛,奇怪地看了我们几眼。当时,真使我有点下不来台,说实话,我真想生气!可是,她又是那样坚决,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她走!
一面下楼,她说:“好贵!这哪里是我们来的地方!”我说:“钱也够了!”她说:“不!一顿饭吃好几斤小米;顶农民一家子吃两天!哪敢那么胡花!”
出了饭铺,我默默地跟着她走来走去,最后,在街角上的一个小饭摊上坐下了!还是她先开口,要了斤半棒子面饼子、两碗馄饨。大概她见我老不说话,怕我生气,就格外要了一碟子熏肉,旁若无人地对我说:“别生气了!给你改善改善生活!”
像这类事,总还可以容忍。我想一个“农村观点”十足的“土包子”,总是难免的,慢慢总会改变过来……
哪知她并不!
那时,机关里来了不少才参加工作的新同志,有男的也有女的。她竟不看场合,常常当着他们的面,一本正经地批评起我来。她见我抽纸烟,就又有了话了:“看你真会享受!身边就留不住一个隔宿的钱!给孩子做小褂还没布呢!一支连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东要一把烂烟,和上大芝麻叶抽,不也是过了?”
开始,我笑着说:“这可不是在抬头湾啦!环境不同了呵!”
她却有了气啦:“我不待说你!环境变了,你发了财啦?没了钱了,你还不是又把人家扔在地上的烟屁股捡起来,卷着抽!”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的脸刷地红了!站在一旁看热闹的青年男女同志们,本来看得就很有兴趣,这时候,就有人天真活泼地嚷起来:“哈哈!脸红啦!脸红啦!”旁的同志也马上随声附和,并且大鼓其掌:“红啦!红啦!”这一嚷,我的脸,果真更加发烫了!
我发觉,她自从来北京以后,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她的狭隘、保守、固执……越来越明显,即使是她自己也知道错了,她也不认输!我对她的一切的规劝和批评,完全是耳边风!常常是,我才一开口,她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来难我:“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等等。她所说的确实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弄得我也无言答对,这样一来,她也就更理直气壮了,仿佛真理和正义,完全是在她的一边;而我,倒像是犯了错误了!她几次很严肃地劝我:“需要好好地反省一下!”
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呢?我自己固然有些缺点,但并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除了沉默,我还有什么办法?可是,有一次,我忽然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们破例吵了一架,这在我们结婚以来,还是第一次。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