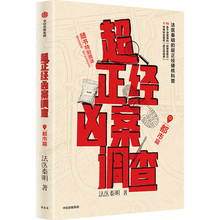本以为进行常规的消毒处理后就应该没事儿了,哪想在下学期的例行体检中,这倒霉小子竟不幸被查出了艾滋病。这小子从娘胎里爬出来也二十几年了,例行体检也不下几十次,要说是母婴传播没道理之前查不出来,也不至于有那么长时间也没发病。吸毒那更是不可能了,我们三个都是101%的大好青年,平时连烟都不吸。再说他长得肥头大耳的也不像是需要输血的料,献血?他又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剩下的也就只有性交了,我们三个住在一舍一楼111寝室,真是应景儿,全是光棍。这么说来,这小子要不是去找“鸡”的话也没有别的途径能感染了。我和常来想了想,他就算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儿啊。更何况,这伙计又是个绝对的禁欲主义者,每次我和常来躲在寝室里看黄片,他都会很鄙夷地瞟我们一眼,嘟嚷一句“欲望啊,俗”之后就滚床上睡觉了。<br> 忙活完手里的活儿,常来拉我出去走走。天气死热,真是不愿动弹,何况是和他这么个大老爷们儿,要是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那可就另当别论了。<br> 出了校门后,常来从兜里抽出根烟来递给我。<br> “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抽烟啦?”<br> 他也不理会我,又抽出来一根塞进嘴里,很熟练地叼着,苦笑了下。摸出打火机点烟,点完把打火机递给我,狠狠吸了一口,又把烟雾徐徐吐出来,吐到一半呛得连续咳了好几声。<br> 我摆弄着手里的香烟,中南海。<br> 溜达过了几条街,是一个小古玩市场。弄一堆破铜烂铁摆在店面前的摊位,其实并没有什么人会停下来看一眼,真正的买卖都在里面偷着进行着呢。古玩市场不同于菜市场,基本上没有“扎堆儿”的现象。“看那儿,怎么围了那么多人?”常来把烟头扔在地上又用脚蹑了跟。<br> 街道的右侧有个摊位前围了几层人,像是有热闹看了。我们俩紧走几步凑了上去。<br> 人群最里层的摊位前跪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儿的身前摆着一个大坛子,用白色乳胶样的东西封着坛口,看上去密封的程度不错。盖子上写着红色的大字:罪。很容易看出来,真的是用血写上去的。围观的人群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说句不好听的,酷似一群无聊的大老爷们儿围在一块儿看脱衣舞。<br> 看来是有热闹看了,我和常来兴致颇高地钻进了人群的最里层。就在这时,从摊位后的店面里冲出来一个“秃头”,三两句脏话就哄散了人群,还冲着那白胡子老头儿无奈地叹了叹气。<br> 这“秃头”的光脑袋倒是挺别致的,头顶上有一块血红的胎记,酷似一只小脚丫的形状。<br> 常来歪着脑袋在那个“罪”字上端详了一番,懒散地念叨了句:“这里装的什么玩意?”<br> “秃头”冲我们摆摆手,不耐烦地嚷嚷着:“去去,一边儿看去!”<br> 自从大彪住院,常来心里一直就不爽,一听这话立马就火了,“怎么?怕看啊?你以为是你们家的宝贝啊?管得着吗你?靠!”我怎么扯他也没扯走,两人差点儿没动起手来。<br> 就在常来和那“秃头”剑拔弩张的时候,白胡子老头儿从地上站了起来,又拉开了两人,随后,他把我们俩叫过去,“来来,俩小伙子。”他用干巴巴的手指指着身前的坛子,声音中夹杂几分沧桑感,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老头儿放慢语速,徐徐说道:“这里装的是手指头,一坛子手指头。”说话时眼睛一直在瞪着,真担心那浑浊的眼珠子会突然掉下来摔成八瓣。<br> 常来借着方才的火气继续嚷嚷:“手指头又怎么着?想吓唬我还是,怎么着?告诉你,老子可是医学院的,别说是手指头了,老子我见过的死人恐怕比你见的活人都多。”这牛皮让他吹的,无语了。<br> 那“秃头”极度无奈地摇了摇脑袋,转身朝着摊位后面的店里走去了。白胡子老头儿抿着嘴笑了笑,朝我们俩打量了一番,“孩子,我给你们俩讲个故事听听咋样?”这笑,让人看了觉得阴森森的。<br> 老头儿的话音刚落地,走出几米远的“秃头”赶忙折回步子来,快步走过来往路上推我和常来,“走吧走吧,可别招惹他了,·他一讲就没完没了,我还怎么做生意。走吧走吧。”<br> 常来一把甩开“秃头”的胳膊,“一边儿去,就听!”这小子一直就这么犟。<br> 白胡子老头儿厌恶地瞟了“秃头”一眼,数落他说:“四驴子,你爹怎么教你的?这么没礼貌!”那“秃头”似乎也没怎么生气,就是一脸的无奈,气呼呼地转身走掉了。<br> 白胡子老头儿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胜利的喜悦,拿过摊位旁边的马扎坐在上面,整了整衣襟,又清了清嗓,开始给我们讲了起来。<br> 这是一个关于“盗尸”的故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