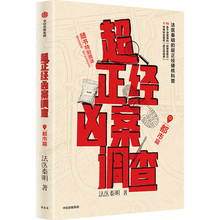1 剖腹取货
昆明到上海的列车缓缓驶进站台。大量乘客涌出。
此时已是半夜12点多。月朗星稀。夜幕下的上海交织着灯火的光柱。烟霏云敛。
2003年仲夏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灼人的热浪,温度上升到令人眩晕的程度,让人感到闷热异常,暑热难当。
车站的广场上,一个瘦长男子脸上淌着汗,朝四周望了望,摸出手机,与人通话:“大姐,我已出了火车站,饭碗没打碎。火车上,我倒是看见有些倒霉鬼被警察拎走了。”
“找家小旅馆或招待所,当心点,给手下人上上笼头,打打预防针,念念紧箍咒。”对方吩咐。
“我明白!”瘦长男子如奉圭臬地点头躬身,仿佛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就在眼前。他收起手机,摆着架子向后面站着的几个人挥挥手。“走吧!不要木头木脑,也不要毛手毛脚,懂点规矩。谁把事情搞砸了,弄得喇叭腔,就对谁不客气;谁当刺头儿就扣谁的钱,到时不要怪我。开房后,不要炒料豆乱嚷。”他倒秧田地重复道。
他很庆幸在火车上乘警没有盘查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打量了一下就离开了,要是真查的话,他也不怕,不会有证据落下,他自认其手法是万无一失的。
在一家小招待所里,一位四十岁开外的总台女服务员正在伸懒腰打哈欠,显得疲惫不堪。招待所的大门敞开着,夏夜的微风有气无力。路人已经稀少。
这时从门外走进二男三女。
领头的就是那个在广场上打手机的瘦长男子,三十多岁年纪,两只肉眼,长在一副铁石心肠的面孔上。他衣着光鲜。后面跟着三女一男,看模样都是乡下来的,虽不是衣衫褴褛,但都是土头土脑、未见过大世面的模样。拿手机的男人以狞视的目光管束着这些人。
一个女的较胖,另一个女的较矮,第三个女人较瘦,那个男的也是农村人的外貌,四个人都是三十左右的年龄。他们虽都一脸倦容,但还是不时好奇地东张西望,打量这陌生而楼宇林立的地方。
见有旅客进来,总台服务员站起身,无精打采地问道:“开几间房?”
“一间。”领头的男子回答。他的脸上挂满汗珠,其他人也汗水涔涔。
“一间?这么多人只开一间?”她懒眼扫了一下这帮人。
领头的男子把手搁在台面上说:“只要一间就够了。”服务员奇怪地问:“五个人一间房,怎么睡?起码要两间才行吧?”
他解释道:“我们只是歇歇脚,天亮就走,只几小时。”服务员说:“丑话说在前头,住几小时也是以一天来结账的,不要退房时计较不清。”男子一口答应。看得出,这男子不是第一次住这样的招待所。
服务员把圆珠笔放在单子上,让来客填一下登记单,并要他们把身份证都拿出来。对于这些身份证,服务员只瞟了一眼也不一一核对,就还给他们。
“身份证不用登记?”领头的男子有几分意外。
“填一个人算了。”服务员伸了伸腰肢,舒展一下筋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填完登记单,付好钱后,服务员拎起一串钥匙,领着一行人走上二楼,打开左边的一问客房关照道:“已经很晚了,客人都睡了,你们尽量轻点,不要影响别人。这天也太闷热了,休息吧!”
“知道,我们不会弄出声音,你放心。”领头的男子招呼身后的人进房,“轻点,不要说话。”
一行人进入房间后,领头的男子关上门,立即摸出身上带的药和包里的矿泉水递给他们:“快!把这泻药吃了,争取天亮前完事,抓紧时间。”
四个人战战兢兢地遵命而行。
吃下泻药后,有的斜靠在床上,有的坐在椅子上,悄无声息,静静等待。领头的男子看了看表,已是凌晨1点多。他认为时间足够,一切拿捏得很准,不用天亮,就可大功告成。嘿!使唤这些眼皮子浅、蜗居一隅的池中物真容易,一点不费劲,好操作。
“你们听好了,等一会儿你们会有点难受的,那是正常反应。记住,不要慌,更不要叫,咬咬牙,忍一忍就过去了。”领头男子装腔作势地告诫道,“谁要是弄出麻烦来,就砸谁的饭碗,谁就倒霉。都给我挺住,拉下来!”
胖女人说自己是第一次吃泻药,她很紧张地问:“有多难受,受得了吗?”领头的男子瞪了瞪眼说:“别驴喊马叫的,受得了,咬咬牙,挺一挺。千万不能出声,把人惊动了就要坏事。”
瘦女人缩着脖子问:“要是拉不出来怎么办?”看得出她有点提心吊胆。
“不会的,尽管一百二十个放心。”领头男子给她们吃宽心丸,“泻药下去,到时自然冲出来,拦都拦不住。”
“天亮后就走吗?”这时瘦女人心里已想着离开,感到闷在这间小屋里极不舒服。
“对!拉出来后,等天亮了就出去吃早饭,吃完后立即离开上海,到火车站后我给钱。”
“我们回家里,还是再去云南?”
“拿到钱后,你们就不想再回家了,你们端的是金饭碗,这可是发财的机会,你们走我这条道算是走对了,谁不喜欢孔方兄?孔方兄懂不懂?就是钱!知道吗?钱!以后我会经常给你们补补课。”领头的男子一脸怪相地“嘿嘿”两声干笑,笑声中有种难以捉摸的阴险。用这些人省心,虽然不对脾胃,但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他这样想。“好了,现在谁也不要再嚼舌头多嘴、满世界嚷嚷了,鬼吵庙!也别像缩头乌龟。打起精神,给我拉出来!”
大家相顾无言。过了一个多小时,四人都露出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只煮熟的大虾,深深地弯下腰,难受地用双手捂住肚子。不一会儿,三十出头的男子,第一个捂着肚子冲进卫生问。大约10分钟后,他走出来,双手捧着数十颗用避孕套包扎成鹌鹑蛋大小的海洛因,交给领头的男子,“郭大哥,终于拉出来了,难过死了。”
那个被称为郭大哥的领头男子大号叫郭宝昌,他见了这些东西开心地笑了,两手接过来心花怒放,“你看,没事吧,就这一阵子。”
“刚才非常难受。”拉出海洛因的男子惨白的脸上滚着豆大的汗珠,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
郭宝昌乐不可支地指着拉出海洛因的男子,唾沫星子四溅地对三个女人说:“你们看,熬一熬就完事了,轻松得很!”
郭宝昌把海洛因放进马甲袋,再塞进一只黑皮包里。他觉得用这一招运货,真是最保险的,警方本事再大,也查不出来。比起把货放在包里、在火车上被乘警查到的那些人,他真是高明多了。
这时,较瘦的女人接着冲进卫生问,拉出同样用避孕套包扎的海洛因,交给郭宝昌,“妈呀,总算出来了。再不出来,真的受不了了。”
“好了,没事了,歇着吧!”郭宝昌接过海洛因,又一次绽开虚情假意的笑脸。他心里盘算着,要不了两个钟头,事情很快就能办完,天一亮就离开。看来下一单还是用他们。
瘦女人喘口气,擦了一把汗:“放在肚子里,让人担心死了。”
装好海洛因,郭宝昌拉上皮包的拉链。“你们这样赚钱多容易呵!不费心血,拉出来的是大把的钞票,赚来全不费功夫。”他尖声怪气地说。
较胖的女人和较矮的女人,已痛得大汗淋漓,眼里闪出哀怨、混浊的光,嘴里忍不住发出呻吟声,十分凄惨。
“妈呀,受不住了,难受死了。”
“疼死了!疼死了!”
“快想想办法……”
“不干了,再也不干了!”……
声声哀号,声嘶力竭,那痛苦的情状,仿佛人之将死的苦苦
这时的郭宝昌脸色骤变,脸红颈胀地走到她俩面前,握紧拳头,叫她们不要出声,再坚持一下。他担心深夜里哀叫声会惊动旁人,招来麻烦。
胖女人滚倒在地,声声叫着郭大哥,向他求救。郭宝昌用拳击掌,要她咬紧牙关,不许叫。
“我难受。啊!”那是一种揪心的嘶叫声,郭宝昌恼火地迅速用手捂住她的嘴。
两个女人疼得满脸是汗,浑身湿透,佝偻着身子不时抽搐,双拳时而顶住肚子,时而撑在地上,情状惨不忍睹。
她们为了赚钱,把命也豁了出去。钱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它给人带来幸福微笑,也让人加入被死神召唤的行列。幸福和苦难有时只在一念之间。
就在这时,招待所门口又走进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他问总台服务员还有没有房间,正在闭目打瞌睡的服务员张开矇眬的眼睛,点了点头。
来人填写登记单,付完钱,服务员领他走向二楼,打开右边的一间房。安排好客人正要下楼时,她忽然听到左边的房间里传出一声“快救救我吧,我撑不住了”的叫声。
悲惨的呼喊声使服务员一惊,睡意顿消。她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房间里又传出疹人的痛苦嘶喊,听得她心惊肉跳,脸吓白了,大气也不敢出,她心想,一定出事了,在闹人命案吧?我的妈!
她的心情极度紧张,脑海中上演着各种匪夷所思的联想,猜测恐怖的细节,越想越怕,情不自禁地哆嗦起来。
房间里,郭宝昌又捂住矮女人的嘴,让她闭上嘴巴,不许出声。他被两个女人的哀号搞得心烦意乱,一筹莫展。
矮女人嘶哑着嗓子喊:“郭大哥,实在撑不住了……”
郭宝昌没有一点慈悲和怜悯,反而凶相毕露,横眉怒斥:“再像野猪号叫,别怪我不客气了,现在只有忍,忍到拉出来。”那副恶相像是要一口吃掉她们。
矮女人实在疼痛难忍,“求求你,要疼死了。”泪水伴着哀求声一涌而出。
“死不了,熬过这阵什么屁事都没有。”郭宝昌发狠劲把她摁在墙角。为了尽量不让她发出声音,他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的。
矮女人发出痛苦的喊声,不由自主地双手抓住郭宝昌的衣领。郭宝昌却狠狠地用手捂她的嘴,不让她的声音叫出来。
胖女人痛得直喘粗气,已无力叫喊。她脸色煞白,满身是汗,衬衫像是被水浸过一样,整个人扭曲得变了形,挣扎地喊了一声:“娃儿,妈对不住你了!”
郭宝昌一面捂着矮女人,一面看着胖女人,注意她的情况,不时发出“咬住牙,不要叫,不要叫”的指令。但他的努力已无作用,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惊动旁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