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安河
一
三山膝盖用力抵住地面,双膝一起抵,像下跪,左手与右手则一起直直往下压,一下,两下,三下。现在陈三山把手往上举了举,举进自己的视线,这个动作是为了回忆。究竟几下呢?压了几下?真的想不起来了。也许五六下?如果一下按三四秒钟计算,那么,他的手在女孩乳房上也仅仅停留了二十秒钟左右。短暂的二十秒钟后,他可能也无望了,收了手,直起身,马上又俯下去。他张大了嘴,湿漉漉的还留有水珠的嘴非常急切地向女孩的嘴凑近,两只巴掌还揪住她的上下唇,想将嘴掰开,在自己的嘴抵达之前,把她的嘴掰到最大。
春末这个眉眼清淡的上午,阳光很稀,一张薄纸般铺在天空。陈三山撅起头先是吸一口气,张大嘴,瘪进肚子,如同一部马力超强的吸尘器,狠狠一吸,要把天地间所有的空气吸光似的,然后才合上唇,凑到女孩嘴上。一张男人的嘴和一张女人的嘴在一群围观者的眼皮底下,紧紧粘到一起。三山要干什么?咕咕咕,他忙着吹气,咕咕咕,吹进去,再吸,再吹。这次三山记得,总共只吹了两次,正想吹第三次,有人叫道,110来啦。接着有人又叫,120也来啦。警笛拖腔拖调地叫,有点虚张声势。陈三山抬起头时,一股红蓝黄光交替旋转着扑进眼。
好了,警察和医生都来了。从水里捞上来的女孩,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她等待的不仅仅是三山,很多事三山完成不了。
陈三山从地上站起时,仔细睃一眼四周,却什么都没看清,眼仍花花绿绿地晃着红蓝黄光,这三道色泽像从瓶子中漏出的颜料,刚才,在他抬头一瞬间,渗进了眼,把眼球染了,一波海水,一波火焰。
那个人是谁呢?叫110来啦、120来啦的人?如果他不叫,三山是不是真的会把嘴不断贴下去,贴住女孩,一口一口地吹?三山没有把握。木穗提出的也是这个问题,她说,如果人家不叫,你是不是会一直干下去?
她使用了一个“干”字。
公平地说,木穗看上去一点都不像生气,甚至别人都从她脸上看到高兴,因为她确实笑了,眼睛眯成一条缝,弯弯的,像被现代美容术精心美化过的韩国女人。笑起来眼睛像韩国女人那么弯着是木穗标志性的表情,细细的弧线,匀称、柔和、妩媚,既没有直线的僵硬,也没有曲线的凌乱,这是弧线的独特魅力,具体表现在眼睛上,就更加让人心荡。可是现在,她的笑让三山头晕,迷离的笑意丛中,这个“干”字并不像说出来的,而像一枚竹针,从她肚子里尖尖地飞出。三山觉得眼睛被刺中了,立即就转了视线。如果三山把视线转得从容一点,还不算失态,但那一瞬间偏偏他心一乱,一下子就垂下眼睑低下头,视线落到脚尖上。何必这样呢?三山定定神,准备抬起头镇静自若地正视她,她却先开口了,她说,噢,雷锋叔叔!
她噢得非常夸张,嘴撅起,弄成一个“O”形图案,而且定格下来,两颊因此有些变形,老妇人般凹进去,凹出两个边缘清晰的坑。
依娇正倚在椅子上,脸对着镜子往外看,看到木穗瘪着腮帮叫三山雷锋叔叔就笑了。
三山感觉很不好,也说不上哪里不好,虚虚的,就是不对劲。他说,依娇,别笑!依娇不听,笑得更大声,马毛似的金黄色披肩发欢快飘动。
她说,陈三山,你真的这样。她把两臂撑直,推几下,嘴又撅起,还往前噜,做出亲吻的动作。这样,真的这样,你是这样的。
她这么做的时候,木穗很认真地看,一边看一边继续笑。
三山叹口气,他想,还是说说过程吧,把过程一步一步地还原出来,让木穗知道,他的手无论按在哪里,他的嘴无论怎么与女孩对上,总之,无论如何,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木穗,他叫了声,叫完,咂咂嘴,好像那上面粘着一层膜,得舔掉,话才可能说出口。他说,是这样的……
是啊是这样!木穗打断三山,她的食指弯钩般翘起,一下一下点着依娇,说,就是这样,嗬嗬,这样,我知道了。
三山急切地把手从上往下一砍,又一砍,肩胛处嘎嘎响两声,可能用劲太猛了,臂膀像条蛇似的在空中舞动,恨不得脱臼跑掉。三山说,过程是……
陈三山你真是的,何必呢?木穗又笑,她眼往前望,望着店外面的路,再望到路旁边的河。河现在很安静,刚才却不静,刚才闹得跟地震似的。
三山问,什么意思,何必是什么意思?
木穗说,你不知道?何必就是何必嘛。
三山咽一下口水,喉结像一团圆球上下滑动,滑得可能有点反常规,过于迅速了一些,所以木穗一直盯住那儿看,看着,照样笑。三山说,木穗,这事要说清楚。
木穗睁大眼,很诧异的样子。难道还不清楚?她回过头问依娇,啊?还不清楚吗,依娇?
依娇走到木穗旁,一条胳膊搭到木穗肩上。她说,太酷了,扑通,陈三山一下子跳下去,水一下子就浊了,人一下子就救起来了。可惜,不知道有没有救活。
木穗说,可惜我没看到。
二
木穗没看到的是整个过程。
过程是这样的:
上午十点左右陈三山在店里,依娇也在店里,只有木穗去超市了。超市木穗每天只去一趟,所以她去得很仔细,从蔬菜柜逛到鱼肉柜再到水果柜,一样一样慢慢比较细细推敲,心里温习着食谱中的各种最佳搭配。
店里当时有一个客人理发、一个客人洗头,理发归三山,洗头归依娇。三穗梳剪坊是三山和木穗结婚后第二月开起来的,已经开了两年,也就是说三山与木穗已经结婚两年。店址选在晋安河边,店里没多请小工,小工只有依娇一个,还有点不太正式的味道。依娇比较正式的身份是木穗的表妹,高中毕业后在家闲着没事,木穗就让她来帮忙,反正洗头又不需要手艺,怎么舒服怎么挠就是了。
依娇有长长的手指,还有与木穗类似的弯弯半月眼。依娇抱着客人的头挠呀挠,挠得人家正云里雾里,突然听到了一串叫声,跳河啦跳河啦!声音刚开始有些模糊,像从电视里传出的,像某个韩剧的夸张对白,三山和客人都没回过神,连依娇也没在意。但很快,有人在路上跑起来,往同一方向跑。噼噼啪啪,水泥路面被一双双鞋敲击得像一面鼓。依娇往店外探出身子,伸长脖子,屁股翘得极高。依娇的身体语言最经常使用的首先是屁股,其次是胸部。她发育得很好,根本无需动用电视广告推销的任何一款药品,就已经能够做一个挺好的女人了,对此她很满意,看到哪位女星扁平的胸口就啧啧啧一阵诽谤。因为沾着泡沫,她把十指朝天举起,像举着两束爆米花。干吗呀?依娇问一个跑过的人,那人是隔壁陆羽茶庄的杜老板。回答:有人跳河了!
跳河不是小事,三山在晋安河边已经两年,却第一次碰到。
对于第一次碰到的事,通常最初的反应是缓缓的,缺乏真实感,就像火车刚刚启动,轮子总是转得犹犹豫豫,等转了一阵,终于就理直气壮地越转越快越转越坚决强烈了。
依娇丢下客人往外奔。她十八岁,还是个孩子。来洗头和来理发的两位客人年纪都在四十岁以上,他们也从座位上站起。理发的已经接近尾声,他看看镜子,说可以了可以了,就自己扯下围布,边拍打着脖子上的细发针,边快步往外走;洗头的还仅仅处于初始阶段,一头的泡沫让他难受,他围布在身,白泡沫在头,模样古怪地到门外站一会儿,犹豫了片刻,终于还是好奇心占上风,双手揪着塑料围布的边缘小跑进来。先冲一冲,冲掉泡沫,一会儿再洗。
三山按他的话做了,然后客人出去,三山掩上店门也出去。他们都到了河边。
晋安河挺宽的,全市四十二条内河它最宽,看上去也最干净。报纸上说,几年前市里搞了一个冲污工程,就是把闽江水抽起,从上游灌进内河,人为地让它加大流量加快流速,流一圈后再回归闽江下游,死水变活水,挺不容易的,多少让人想起愚公移山的壮举。晋安河这么大,吞下的水就最多,每天殷勤地流啊流,三山以为它挺干净的,没想到,却黑了,黑了一圈。杜老板的妻子小丽指着那个圈说,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又说,是个女的。
三山其实只听清前一句话,后面一句也进入耳朵了,但没停留下来。
就是从这里跳下去的!三山被这句话震得毛孔松了一下。小丽所说的这里,是一块草地,草地旁有棵榕树,榕树下砌一个石凳。三山曾经在石凳上坐过,不是偶尔坐,而是经常坐,店里没生意时,三山有时觉得闷,木穗就鼓励他,你出去走走吧,到河边走走。三山果真就去了,嘀哒嘀哒独自走几步路,到石凳上坐下,一坐半天。有时候,水面上有一些碎木片漂过,这往往是雨季刚过不久,三山猜想碎木片也许原先是待在哪座山上的,被冲到闽江,又被闽江带来,它们进城的过程比民工便捷多了,还无需路费。有时候,会突然驰来一只船,很小的船,古书所说的一叶扁舟大约就是这样子,因为它的确窄得像树叶。船不打鱼,也不撒网,是城管雇着专门在内河上捞脏东西的,相当于清洁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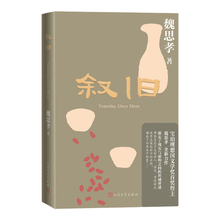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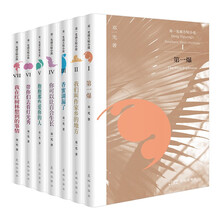




——作家 刘醒龙
吸引小说家北北的.是一种”有病”的生活。换言之,在人们看似平常的事物中.北北发现了生活的反常化……生活与人的反常.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只有深入骨髓的“病状”间或以偶然性的方式出现,已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以为,这就是生活的真相。至少,这是我读出来的,小说家北北提供给我的生活真相。
——评论家 陈福民
北北的小说再一次让我们回到具体而细微的生活情境。市井胡同、建筑工地上的民工,发廊里的打工妹、小偷和妓女、偷渡和走私——北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驳杂的生活景观。更重要的是,从生活的“缺失”到生活的“破碎”,从对”破碎感”的体认到命运之荒诞的揭示,北北提供了她对当下生活情景和精神存在的犀利观察和独特理解。
——评论家 林秀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