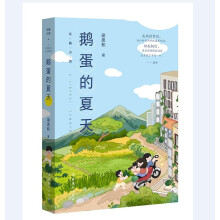The Beginning
当林夜希从轻浅的睡梦里再次醒来的时候,时间像是被期待了无数次的未来般终于缓慢地流动到了圣诞即将来临的时候。
把身体裹进厚厚的纯白色被子里面,空气里弥漫开的是上海冬日里独有的凄冷感。
白色的墙壁上画满了一条又一条长短不一的黑色线条,像围在生命上的漫长监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断掉。
林夜希吸了吸鼻子,小声地说了句:我怎么还不死啦。
南京西路办公楼里的白领们手里拿着刚从老板那儿接过的解聘信,迷茫地望着窗外的花花世界。从明亮的玻璃窗望向斜对面的恒隆,门口提前摆放了一排在灯光下熠熠发光的晶亮圣诞树。
梅龙的新办公楼已经重新装修完毕了,楼下的必胜客里播放着圣诞歌曲,温吞的空调暖气下服务员们都穿着大红色的圣诞装。
西藏南路上巨大的电子荧幕底端循环滚动着一排气象局发布的寒潮警报。
这个圣诞,注定是一个寒冷的圣诞。
就在这之前的一周,雅虎刚宣布全球裁去1500名员工,SONY也宣布裁减1.6万个工作岗位。
时间如果再往前一个月,那就能看到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潘特宣布裁员五万人的计划,法国储蓄银行也裁员4500人,欧洲最大的制造商西门子公司辞退1.68万名员工。
而如果能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回拨的话,那么雷曼破产、美林卖身、通用关门这样的讯息就会从四面八方逼涌过来。
就在小布什即将下台之际,华尔街掀起了惊悚而庞大的金融风暴,又一个黑色九月,如当年的9?11一样,热烈欢送着过去某些的离开。
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完美游戏,无数块庞大的多米诺骨牌连续不断地倒下。
砸起的漫天硝烟沿着大气层包覆起整个孤寂的星球。
当每个人还在平静地生活时,看不见的洪流黑暗已经在阴影里肆意地疯狂滋长着。
直到破土而出的那一刻,金融风暴崩塌性地席卷全球,澎湃的虚无黑洞开始缓慢地吞噬一切。
那些安静如同沉睡的骨牌尸体,全都束手无策地被一点点吞没。
而我们,都只是在黑洞里浮游着的细微生物。
当股价暴跌而导致全球首富巴菲特的资产据传瞬间缩水几百亿的时候,设计总高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却即将开工,以真实的狂妄姿态超越金茂和刚建成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当之无愧的成为上海新的华丽风向标。
早晨街道上刚刚运到书报亭的报纸还散发着浓郁而新鲜的油墨香,在尚未被蒸发的晨露中安详地等待着什么。
方正的字眼冰冷地描述着逼仄的现实,或许是《金融危机致使世界首富损失惨重》亦或者是《中国第一楼横空登陆陆家嘴》。
只是无论如何残酷或华美的报道,都会在半小时之后随着报纸一起被遗弃在一号线的地铁车厢里,或是某个没有被编号的垃圾桶内。
因为那些被版印起来的生冷报道,永远都在人的意识里被无限地推远。
虽然都知道是遥远的,却又无限期的在每一个胸腔深处逼涌起无数的冷漠。
而即将构建的上海中心大厦,如同又一块插入陆家嘴的华丽骨牌。
巧妙的视角下,整座城市就像一套精美而死硬的模型。
上海,庞大而光芒四射的一座多米诺之城。
上海的气温骤降,冬天陡然来临。
楚晴裹着那条MANGO的羊毛围巾站在风里,看着无数对情侣手拉手走过来福士门口那些五光十色的圣诞树。
她知道,所有人,此刻都在前所未有的危机中煎熬……
而星巴克巨大的蓝色落地玻璃窗后面,方明泉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叶蓉,心脏上像是被掏空了一个大洞,然后被灌进了一整个冰川世纪的寒风。
对面街角的书报亭里还挂着PSP平台上去年上市的一款火爆游戏的海报。
3D技术创造出来的萨菲罗斯面容精美而冷漠,让他想起了《迷黎》扉页上夜夕那苍白冰冷的容貌来。
而萨菲罗斯的头顶印着一行银边的白色英文字母。
FINAL FANTASY——最终幻想。
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地怀抱希望,等待着新时代的来临。
光明的未来时代。
却不知道次世代的涵义,是只有被不断期待却永远无法到来的未来时代。
上海最冷的冬天终于来了。
Who are waiting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First
[four months ago]
飞机颠簸了几下,楚晴有一种灵魂被抽离出去的错乱感,于是就摘下了黑色的丝绒眼罩。
她伸了个懒腰,头等舱里新鲜的空气随着呼吸流遍四肢百骸,有一种初春时突然涨潮溢起的春水开始缓慢流淌过积雪,一点~点消融成冰水的感觉。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回来心脏上像是挂满了尚在滴水的冰尖柱,凉凉地穿透过血脉的纹路。落在柔软的身体深处,在黑暗里积蓄成一池湖泊。
头顶的扬声器里低低飘落下空中小姐软绵绵的声音,似乎在说飞机就要降落了,请各位旅客系好安全带。
从天空里望下去,脚下这座庞大的城市像一套精美好看的塑料模型,涂着七彩斑斓的颜料被摆放在明亮橱窗最醒目的位置。
从底下打亮的金色光线包裹起一切。
楚晴从口袋里摸到一张照片,照片上她自己和另一个金发女生并肩站在一起。她伸出纤细的手指动作缓慢而有力地把照片一点一点地撕碎,然后丢进随身的那只Caetier限量兔毛手袋里,这是她上个星期在Sake里面新买的。
她拍了拍手,微微翘起嘴角自言自语道:“Goodbye my memory.”
夏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外暖暖地打进来,拉扯起一道长长的透明影子。
光滑的白色机舱里,缓慢游离着一些浅淡细微的影子。
早晨的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火车站那种拥挤到随时都能闻到汗昧的密集人流不同。
这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总会有提着IBM商务笔记本匆匆而过的人,来到窗口排队换取登机牌;这里咖啡厅的一杯蓝山总比仅是一路之隔的对面要责上一倍,但店家却从来不担忧有一天会没人点;这里各个国家用不同的线条勾勒出来的面孔一定比外滩还要多上很多,操着各国口音但同时都会问一句:“Eecuse me.”
这就好比在路边地摊上总是会看到被胡乱堆放的廉价衣服,而Chanel的专卖店里装修整面白色的墙壁只不过为了挂上~件今年新款的风衣。
这个城市极端的贫富两级分化,把人之间的距离拉扯得像是一个沙漏,仅靠着一个渺小而脆弱的支点来连接。
每一天的生活像是布满了细碎刀刃的沙砾,在平静地流动中把心脏切割得体无完肤。
楚晴边走边用手机打电话给她父亲的专职司机Viken让他来接自己。Viken是个特种兵出生的中亚男人,她十五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她父亲的专职司机和保镖,那个时候也正是楚天翔挤进上海滩一流房地产商的时候。
如今已经二十二岁的她,却早已弄不清上海到底有多少楼盘是属于他父亲名下的了。
楚晴一抬头,就看到了两米外的夏渔,正安静地站在稀稀拉拉流动的人群里。
和记忆里一样,依旧是干干净净、个子高高的那个男生,只是头发有些长了点,还染成了好看的栗色。
夏渔就这么望着她,英俊的五官被窗外打进来的光线照出了峡谷般深深的轮廓,被阴影覆盖住的整个眼眶里目光像是夕阳般温暖而又柔和。
夏渔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直走到她面前,然后把插在口袋里的双手拔出来,紧紧地环抱过来。
“你回来啦!”声音温柔得像是冬天空调里吹出来的暖风。
楚晴把脸贴在他的胸口,鼻子里是那熟悉的薄荷香气,隔着白色T恤舒服的面料,夏渔胸膛里沉重而有力的心跳,像是从遥远的记忆里传递过来。
楚晴闭上眼睛,紧紧地抱住他。
“是的,我回来了。”
日本语里面把那个尚未来到的时代叫做次世代,象征着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期望。
但其实,对我们而言过去也都是曾经的未来时代,曾经的次世代。
当闹钟响的时候叶蓉出于生物的本能伸手关掉了闹钟,然后把毯子拉过头顶像具僵尸般继续睡觉。
但只是过了一分钟,头顶上气流涌动起的巨大轰鸣声就传了下来。
耳朵里像是被填塞满了棉絮般快聋掉,身体却分明感觉到床在声波里的震动,像是害怕地发抖般吱吱作响。
叶蓉伸手拉掉盖在头上的毯子,一脸倦容地睁开了眼睛。
身边还摊着两本教科书,头顶的天花板中央有些绿色的霉斑,也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春天时下雨渗水的后遗症,墙角有一张挂了好几年的蜘蛛网,只是蜘蛛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叶蓉仰躺在床上,木框窗户里透过来的金色光线像飞扬后落定的尘埃,薄薄地依附在她裸露的肩上。
视野的更远处,一架白色的飞机正渐渐远去。
叶蓉长长地叹了口气,胸口里总是会像是被倒进了一大瓶浆糊般粘稠到呼吸都会淤结了。
住了二十二年的老房子就在离浦东机场不远的小镇上,从小叶蓉就听惯了飞机起飞和降落时发出的巨大轰鸣声。
母亲一直很向往城市里那种公寓式的小区,但越是向往就越只能住在这种老旧的房子里。逼仄阴湿的环境里,让人的心也越来越阴沉,邻里间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得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常有的事。
每每母亲埋怨父亲的无能,叹息自己嫁错人的时候父亲都只是低着头,沉默不语。
小的时候叶蓉最喜欢在弄堂口看着白寥寥的天光照亮整条弄堂,毛茸茸的光影轮廓让她觉得好漂亮。随着逐渐长大,她开始希望能拥有一间挂着粉红色蕾丝纱帐的房间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