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那些青涩的岁月
据说,在大学校园里,最好玩而且最重要的是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这个理论对于初出茅庐的我而言,是那样的神秘而美好。
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适逢全国人民喜气洋洋迎接过的亚运会闭幕,我刚满十七岁。
当我拎着行李站在宿舍门口时,郁闷得只想用头撞墙。我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抵达上海,傻头傻脑、低眉顺眼地混进某医科大学的校门,风尘仆仆地站在女生宿舍楼的传达室门前,可是寻遍了墙上张贴的新生名单,也没有发现我的名字!
于是,我不得不拎着行李到了系办公室,向老师汇报道:“老师,我找不到自己的房间号码。”
年轻的老师很是诧异,断然道:“不可能,我看看我这里的名单,你叫什么名字?”
“林立夏。”
老师皱起了眉头,“林立夏?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
对于这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我早就回答得得心应手,不过还是装作羞涩的模样,说:“报告老师,我是立夏那天出生的。”
老师抬头,非常警惕地看了我一眼,“你还真叫林立夏?我只记得有个林立果!”说完,老师又迅速地低下头,在名单上寻找我的名字。我百无聊赖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东西,忽然发现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家伙,他正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我,在无意中对视上的那一刹那,他迅速地把目光转开,注意力又回到了手中的一张纸片上。我注意到他身高腿长,浓眉大眼,穿着名牌T恤和牛仔裤。
老师总算发话了:“咦?是没有。怎么回事?你是我们口腔系的吗?”
我欲哭无泪,没有搞错吧!这时,一个声音忽然冒了出来:“老师,好像分错了,她在我们班男生的名单上,您看看。”刚才那个坐着的家伙站起来,将手中的名单递过去。
我沮丧到了极点,真是出师不利。
老师嘟囔道:“怎么会搞错了呢?后勤的办事能力太差了!”他总算发完牢骚,喝了口水,对着名单琢磨了一下,“这样吧,韩宇,你把她带到女生宿舍,安排到523房间,那里目前只人住了三个人。”
我和韩宇一前一后走出办公室,他简直就不理我的死活,大步流星地飞奔着,我拖着我的行李一步三摇地跟在他后面。
爬楼梯的时候,他总算等了我一会儿,抱着膀子问道:“需要我帮忙吗?”
我看了看他那张倨傲的脸,摇了摇头,因为我最亲爱的老爹曾经说过:“谁都不欠你的,凡事就应该靠自己。”韩宇却仿佛没有看见我的婉拒,自顾自地拎起最重的行李,向楼上走去。
等我拖着剩下的行李爬上五楼,站在523宿舍里时,我满头大汗的模样和某人的悠闲自若简直就是鲜明对比。韩宇向房间里忙碌的三个女孩子简短地转达了老师的意图之后扬长而去,剩下三个小妞围将上来,唧唧喳喳地问个不休。后来,其中一个貌似老成的女生皱着眉发言道:“你刚从火车上下来吧?瞧你衣服上脏的,嗯,好像都有味了,快去洗洗。”另外两个一高一矮都是圆圆的脸蛋的女生冲着我微微一笑,道:“你先去澡堂吧,澡堂再过一个小时就要关门了。”
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个房间里,除了我是外地来的学生,她们三个都是上海生源。不过,老成的那个是上海郊县的,另外两个圆圆脸都是知青的后代。
她们倒是很热情,转眼的工夫,已经改口叫我立夏了。那个貌似老成的女孩儿叫江宓,于是她的外号——“江米条”不胫而走,糟蹋了她原本非常诗意的本名。而另外两个知青后代,男生们早给她俩起了绰号,一为“大胖”,一为“小胖”。就冲这俩外号,就知道她俩对饮食文化颇有研究,是我欣赏的类型,于是,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和她们混成一团,三只“蝗虫”就这样厮混在一起。而江米条同学对我们的抱团行为颇为鄙视,她有些不可捉摸,总是行踪飘忽,神出鬼没。
我原本对大学生活有无限的憧憬和好奇,可是当跳进“火坑”以后才发现,现实和理想有那么大的差距。医科院校本来就袖珍,在上海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我们这个医学院的地盘简直小得可怜,与我之前就读的全国示范重点中学相比,那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伤心总是难免的,也只有在伤心的时候,我才会无比想念和我一同打发中学时光的那群死党,而最最想念的那一个就是我的发小儿——小米。
小米从小就和我在一起厮混,小学时她当大队长,我当小组长,虽然家庭情况不同,但我们都在一堆大孩子的“强权”下“苟且偷生”;初中时,我俩居然还在同一个班,互相攻击对方,偷看彼此日记,一起买明星的小贴画,一起偷看琼瑶的小说……这些都发生在我们身上;高中时,我俩仍然混在一起,就算高一那年被分在了不同班级,但我们依然相约一起去看那些爱情电影。高二、高三她更是坐在我旁边,成日里窃窃私语。她比我还喜欢发呆,经常双眼失神地凝视着前方,被我一巴掌拍醒后,她总是茫茫然一片恍惚。然而,这位经常神思恍惚的少女,却是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女生。有时,我以为她只要冲我扬扬眉,我就知道她眉毛底下的潜台词。
老牛是我的另一个好朋友,据说在他看似粗犷的外表下,颇有些细腻的感情。可是,他对我和小米这两个从小一块儿摸爬滚打、共同长大的同班同学,态度很是粗暴,特别是在某些美女面前总是贬低我们,借以衬托出美女的高大形象,这让我和小米很是不满。不过,不满归不满,该帮忙时我们一向都帮的。
这两个家伙纷纷考取了理想的、名声显赫的工科院校,虽然学校不同却都位于北京,离我十万八千里。
还有淘气的张率……想到张率,我暗自叹了一口气,因为他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一段我不愿意想的痕迹。
大一上半年,我们一直上大课,所谓大课就是几百号人挤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上课时,除了宿舍的那几个家伙,我可真是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就连到校第一天见过的韩宇也湮没在茫茫人海之中。听着上了年纪的教授用半咸不淡的上海话照本宣科,可怜我这双耳朵,竖得笔直也没听明白老师到底在讲些什么,甚至连他断句断在哪个位置都值得商榷。
郁闷啊!既然无所事事,我只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回信热潮之中,全国各地的邮递员叔叔都要背着我的信寻找它的主人。我把我对学校的抱怨和不满都一一倾诉在信纸上,还有我对小米同学的思念之情。
小米在学校的日子好像并不比我好,至少她在回信里哭诉“我宁愿待在我们家的卫生问里,也不想来这个破地方”时,我心中终于有了一丝安慰。当然,像老牛这样没心没肺的同学是另外一回事,自从他步入那所号称“水母”的校门后,恍若鱼儿遇见了水,满篇的信纸都化作他的笑脸,真是虚荣!
在我最空虚的时候,我和大胖、小胖结成了同盟,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为满腔的饮食动力,除了每一顿正餐,还有点心、夜宵、零食。就在这样的无拘无束、肆无忌惮的生活中,我由入学时又干又瘦的“黄瓜条”,蜕变为学期末又白又胖的“大苹果”,可是我却不以为意。
像我这样不学无术的女子,上课时毫不专心,下课后却生龙活虎,尽管胆子还是很小,彼时的性格还很内向,却并不妨碍我在宿舍里和同学聚众打八十分。
到了学期末,班里居然还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八十分大赛。就在这个时候,韩宇重新进入我的视线,因为签的时候,我和韩宇分在了一组。
他仿佛已不记得和我打过交道,斜睨了我一下,“你行吗?
我头也不抬地入座,正襟危坐,沉默不语。
趴在一边准备观战的小胖乐了,“立夏可不是一般人,在女生宿舍也算打遍天下无敌手,她喜欢算牌,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就掉进她设的陷阱里。”
韩宇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战争总算打响,我们从周日的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杀得昏天暗地。刚开始的时候,我和韩宇配合得不太默契,挨了他数个白眼,后来还有一次我计算失误,他沉着一张脸一言不发,这些情景我觉得是那样的熟悉,想了半天才得出结论:他和张率那厮一个德行。
虽然开始时我们赢得有些磕磕绊绊,但后来过五关斩六将赢得分外痛快。我们一路拔营扎寨,直到冠军到手,韩宇总算给了我一个笑脸,但他却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你都吃什么了,怎么胖了那么多?”作为一个大一的“土包子”,我还没有意识到买一面穿衣镜的重要性,在胡吃海塞中任由自己的体重蓬勃发展,却毫不知情。
对于这种不识时务的家伙,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他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白了他一眼,没说话。
然而,韩宇的第二个问题却让我异常诧异:“你真的是立夏出生的?”
我点点头,说:“没错,如假包换。”
我以为他会再说些什么,却发现他紧闭双唇,沉默不语,我心中一阵忐忑。
比赛的奖品是两盘磁带,一盘谭咏麟的,一盘张国荣的。由于受老牛、张率等人的影响,我喜欢老谭的歌喜欢得一塌糊涂,于是举着老谭的磁带问他:“我挑这一盘,行吗?”
他斜睨了一眼,一把将张国荣的磁带揽入怀中,从嘴里挤出一句:“现在居然还有人听谭咏麟的磁带!”傻子也能听得出这句话如果不是讥笑,那就是嘲讽。
从此以后,他的举动会偶尔落入我的眼帘。
韩宇比我大半岁,总是带着他招牌式的倨傲表情,目不斜视地在校园中穿行。他也从来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就连我们去共青森林公园骑马,他也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自寻节目去了。
我也从同学的谈话中知道了韩宇是北京人,难怪人家一身的大义凛然,原来带着天子脚下的尘土,自然与众不同。
不过,因为这次八十分大赛,我和韩宇熟悉了很多。有时,我们会在阶梯教室的走廊上擦肩而过,或者在图书馆阅览室偶有碰面,彼此都会佯装礼貌地点头,点头次数多了,也会瞎聊几句。
寒假来临,我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父母身边,当然,还见到了和我交好的那一群臭味相投的死党——机灵的小米、狡猾的老牛,以及书生般文静的林晓军、活泼好动的陈文、漂亮的风儿以及成天教训我的张率。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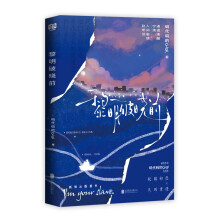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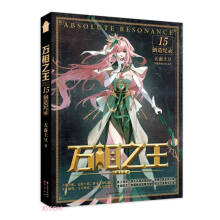





--开心
意阑笔下永远有对青春的不舍,她的青春特别的美,她的友情特别的真,她的恋爱特别的甜,她的故事特别的澄澈透明,看得我很羡慕很羡慕。
--bee
那些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却还牢牢记在心中的青春岁月,那些曾经喜爱的人,那些书,那些电影,那些事情,在这篇小说里总是不经意地出现在你我面前,让人好生欢喜。
--doodle
医院白色冰冷氛围无形中为此职业赋予了一份神秘感,但某天通过读意阑的文,发现白大褂外衣下的人们也爱好八卦、性格幽默,不禁莞尔。
--恬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