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唯有真名实姓是个忌讳
斑点狗像一只受惊的兔子,溜出录像厅。出门后老半天,他还感到手在发麻,心尖尖像被冰水泡过。
斑点狗不是一条狗,是从一个叫黄狗恋窝的村子里出来找活干的汉子。也可以说,是他父母当年没有经验,一次不成功的避孕结的一个果。他从小身上长斑,斑灰白,脱皮,奇痒,他妈李兰香没有少给他吃药打针,但都没有效果。他走到哪儿挠到哪儿。还别说,这手啊,运动多了就特活泛,他从来没有学过画画,居然能画好多东西。一天早上。他在自家的竹山里对着那头老黄牛刚刚摆画架,他爹就发话了:“画牛,很好啊,以后你就和牛一样吃草吧。”他知道,爹不高兴了,在埋怨自己没做什么正事。于是,斑点狗在家呆不住了,跑了出来寻事做。李兰香也急啊,二十五岁的崽还是单身,如果有个好姑娘,让他成个家就好了。但崽就这德行,谁会看得上他?斑点狗自然也是猴儿急猴儿急的,长到二十几岁了,还没沾过女人边,看见异性,他就如同三天没有进食的狗见着打狗棒旁的骨头,饿,但又不敢近前。
斑点狗以前不叫斑点狗,叫苟家思。有天几个人在一起看电视,黑马指着《动物世界》的镜头对苟家思说:“喏,苟家思,你就叫那个蛮好的,斑点狗。”来米也大声叫好:“不错,这个名字特乖,还很洋气,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城市女人的宠物。”于是斑点狗这名字就这样叫开了,先是黑马叫,来米叫,后来录像厅的醉鱼叫,大大小小的熟人叫。
在黄狗恋窝,有几个青年人不是斑点狗的妈妈李兰香接生出来的?人啊,开始都是一团肉,后来才有了名字。名字反正就是个代号,没什么大不了的,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吧。黑马不也只是姓马,还因为长得黑长得帅,一头长发像卷鬃,故被人称为黑马。米加,喜欢过叫什么雪米莉的文章,又整天苦着挣钱给双胞胎妹妹米良和米粒做学费,加之黄狗恋窝称进城来捞钱叫“来米”,也就咋嘘出这一个怪怪的来米的名来了。还有醉鱼,这个余屠户的满崽余全盛,有次为了请人帮忙,拼命喝了八两白酒,醉倒在那个像半边太极图的水塘边,两条鲫鱼吃了他的呕吐物,都醉得露出了鱼肚白,他就醉出这么个名字来。管他呢,该怎么叫就怎么叫,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在别人的城市混,唯有真名实姓是个忌讳。除非,警察要查身份证。警察也有好玩的,比如说前天来的那个鼓眼睛,看模样挺凶,其实人特好,黑马背后就叫他“大姨妈”。斑点狗知道那仅仅是个诨号,不敢乱叫,就常常称他所长。是不是所长无所谓,没有一个城里人不喜欢将他的官职叫大一点。就像醉鱼,开这个小小录像厅,还屁颠儿屁颠儿地直让人叫老板。
斑点狗蹲在街边垃圾筒旁,还在回味刚才胆颤心惊的那一幕。
斑点狗注意这个女孩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这个女孩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特漂亮。怎么个漂亮法不好形容,录像厅光线太暗,斑点狗只能微略看清一点点,就那五官的轮廓,看上去就特好画。她坐在那儿,不停地流泪。录像厅放韩片,女孩被韩流吸纳进去了,全然不知道有一个叫斑点狗的青年男子一直在注视着她。
醉鱼过去不放韩片,放毛片。
以前余屠户在这开屠坊,杀狗宰羊,积攒不少。他满崽醉鱼高中毕业后,在家呆过几年。当时退休老师任实在劝他竞选村干部,他把几个已经报了名的候选人名单一看,冷笑了一声说:“如果选上了,那我反正要和这中间的四个人合作,我啊,还是留着多活几岁吧。”余屠户知道满崽的性格,也没有蛮劝,便想着将手艺传给他。谁知醉鱼才不稀罕这血债累累的行当,他把屠具做了废铁,卖给了废品店的刁德一。
醉鱼算个角。他蹿上奔下,三五两白酒,居然摆平了一络人,开了家录像厅。摆了两台大电视机,一个放像机。两个窗子用厚厚的皮革钉上,墙上只挂两盏昏沉沉的灯,大大小小二十几张凳子。毛片三天换一次,每次就重复播放着两个碟子,生意居然极好。一张碟赚回来的,比他老子杀一头牛还强。
街上当时没有“的士”,只有几百台“踩士”。所谓“踩士”,就是人力脚踏三轮车的美称,冷月市市民出行极便利的交通工具。尤其在城北,没有汽车站,公交车不跑这边,“踩士”就不可或缺了。坐“踩士”也就花一元,远一点的不会超过三元,本市区要到哪儿送哪儿。乡下人最初进城找活干,要是不顺手,男的会先做“踩士”,女人先擦皮鞋,慢慢瞄准了别的事就把这事让给新来的,再改行。
有段时间,“踩士”师傅送完客,无事可做,就买个小瓶子酒斜插在口袋里,挤到醉鱼的录像厅看毛片。花不上几个小钱,过过干瘾。这里,就成了“踩士俱乐部”。
黑马刚出来打工时,也像骆驼祥子一样,做过“踩士”,不过醉鱼不欢迎他。
录像厅被扫黄打非给端掉过一回。
冷月市公安局和文化稽查大队那回是下了老锚。来了一台卡车,七七八八的物什全装走了。醉鱼也像死鱼一样被带上了车。该治的治了,该罚的罚了。
醉鱼最终还得感谢户籍周万里,也就是被黑马叫做大姨妈的警察。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召开听证会,原定要关了这个不正规的文化娱乐场所。大姨妈不同意,他说:“废物,还可以利用,是吧?人难道不可以教育好?两台电视机,一台放碟机,本身没有罪,关键是放什么内容。比如我买了美国的电视机,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是可以的。那个地方,没歌厅,没舞厅,没影剧院,有个录像厅多好,市民有地方看片子,要少打好多架,少打好多牌!这样吧,让他开,我来管牢他,当然,只允许他放正规的。”
大姨妈居然还说动了领导。
黑马开“踩士”去拘留所接醉鱼回时,有些感动地对醉鱼说:“那个警察好,像个温柔的大姨妈!”
醉鱼的嘴一撇,说:“嗤!他呀,我爹杀了这么多年的猪,猪尾巴全是他给叼去下酒了。”
自然,录像厅的生意也就冷淡起来。
于是,醉鱼就琢磨放起了花鼓戏碟子和韩片,没想到录像厅慢慢又升了温。其实,影碟机什么的,现在也不是稀罕物,家家都有,大家之所以跑这来看,主要是家里太冷清。来这,凑个热闹。花鼓戏一般白天放,白天老人多,端着个大茶缸,看《刘海砍樵》、《铡美案》、《十五贯》、《青风亭赶子》,看《三子争父》、《八百里洞庭》、《春草闯堂》、《喜脉案》。边看边议,有时开花圈店的柒婆婆还敞开嗓门大声骂,骂得最多的是不认前妻的陈世美,和青风亭那忘恩负义的不孝子。骂着骂着,话题一转,又骂起了那和陈世美特别相似的某某人,骂现在怎么就没个包公,来铡了现代陈世美。
醉鱼眯着醉眼大声说:“你说铡谁?包公就算是开口了,又谁会愿意当刽子手来铡?什么年代了?你能保证,包公活到现在没个二奶?”大家就哄笑开来,特别快活。
晚上,老人出来不方便,怕闪着扭着。录像厅就放韩片。
韩国佬鬼精啊。唠唠叨叨的,一部连续剧,弄出几十集或上百集,尽是些婆婆妈妈的鸡零狗碎事。歪瓜裂枣的演员,在美容院给弄出清一色俊男靓女。编写剧本的时候,将中国人漠视多年的、老祖宗留下的孔孟之道,细细打磨,研成粉末,制成味精,放到连续剧里煎、熬、煮、炒、烩,居然能让中国的观众,尤其是女人们.一边掏腰包数钱,一边掏手帕擦泪。醉鱼真正搞不懂了,没想到放这种碟也能挣钱。那天来米向他建议时,他还直说她神经病。
斑点狗是来帮刁德一收酒瓶子时,发现那个看韩片的女孩的。女孩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人默默地流着泪,隐隐还能听到她鼻子一下一下地缩着的声音。斑点狗真的不敢相信,在这个黑糊糊的小屋子里,在这么一个粗俗的地方,居然会有一位这样的女孩,一滴水一样,静坐在这里,多好的一幅画啊!她分明比韩片里的女人漂亮多了。
开废品店的刁德一和开屠坊的余屠户刚刚分田的时候就从黄狗恋窝进城打工,算进城开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打工仔”。黄狗恋窝的乡里乡亲,把联产承包叫做分田。当年这两个人物,一胖一瘦,再也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也不怕被扣上投机倒把的罪名。他们拿出了当年智斗余大炮的豪气,一声吼:“我们不怕谁开除我的农籍”,“我们不怕谁划我一个分子”,就一头撞进了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因为瘦,且极像样板戏中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刁满爹这个诨号就得到广泛认同。开始两年,刁德一也只是挑个担子,大街小巷叫唤着:“有旧报纸废书刊烂鞋底破铜烂铁乌龟板子团鱼壳子收么——”日子一长,赚了几个,就不出去跑了,开家店等别人送旧东西来。废品店离醉鱼的录像厅也就两三里路,平时走路过来,也就抽完一支烟,再点一支抽三分之一,就到了录像厅门口。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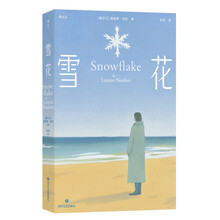

——著名作家 王跃文
世上最感人的事物莫过于人的梦想。中国农民的梦想非常质朴,也非常绚烂。它埋在人的心底,终于要开出绚丽的花来。《乡村候鸟》预示了这个并不遥远的花期。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 何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