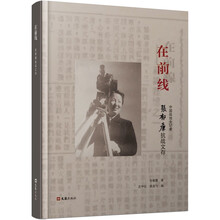逃课人生——我的北大
我生命中不朽的记忆
1995年的1月份,我一个人从西安来到北京,下火车后,就直冲北大了。在北大西门,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位博士生见面。我们之前曾有过书信往来。他热情接待了我,然后带我去北大农园吃饭。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在西安上高中,眼眸里装载了一个少女所有的固执和天真。我第一次去北大,其实是在1994年的夏天,那年7月被邀请参加全国中学生北戴河文学夏令营,因为我的一首诗获得了最高奖“蓓蕾奖”。回西安的时候在北京停了几日,当然顺便去了北大,又拜访了几位老师。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记得当初很多夏令营的营友劝我别那么固执,要现实点,因为他们觉得我眼光太高,太不现实,保送北大几乎不可能。
而我,一个来自西安的女孩子,才十几岁,第一次见到大海我很兴奋,我是不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尤其是生命中的大事,认定了,我不回头。在北戴河,面对阵阵涛声,我许下了我的愿。
走之前,大家互相留言,一位老外也给我留了言,他搞中国文学研究的,他的名字叫戴迈何。他在我的留言簿上写道:“很抱歉我们一没有机会深聊,但愿下次我去西安的时候能够见到你,年轻就是资本,希望你永远不要放弃。——戴迈何。”另外一位作家前辈也留了言:“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我当时满怀期待的,对生命,对以后的路。
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墨绿色的本子,十四年过去了,梦想依旧璀璨,不知北戴河的涛声是否依旧?
高二那年,我曾写过一篇名为“隋系燕园”的文章,后来被《北大校刊》转载,那是1996年的事了。我对北大最初的记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一周以后从北戴河回来,我已经漫步在北大的校园里了。那时学校已经放暑假,学生们都回了家,但校园里依然可以见到行色匆匆的人影。我当时是怀着一种极为崇敬的心情瞻仰这座校园的。北大校园与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尽管我曾多次在报刊上看到那幅著名的“湖光塔影”,如今目睹了她的姿容。记得很清楚,那时正好是7月底,西门内的荷花塘绿荫一片,点点粉莲将夏日的绚烂点染得极富美感。我想这就是北大的夏天了。继续往前走,我发现这里的树很多,小路曲曲折折,我差点迷了路,走之前一位小朋友就告诉我说北大好像是一个大森林,让你怎么也走不出。
听着头顶上的小鸟叽叽喳喳乱叫,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中文系门前。大门已上锁,但“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七个大字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很古典的办公楼,让你能从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中嗅到一种古老深厚极具历史浓度的文化气息。虽然那时我只读高二,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局外人”,但我的心已经完全融了进去。与我同来的一位朋友指着一座不算高的白色建筑对我说:“这就是北大的图书馆,北大的‘一塔湖图’是很有名的。”
我记住了。当时就想,一年以后我哪儿也不去,就上北大。这份心境与这幽雅的环境和她近百年的传统是紧密相连的,而这一切,又独属于北大。
后来带着一份深深的眷恋我回到了西安,然后我读到了那本《精 神的魅力》,于是就有了那篇《情系燕园》。
95年的元旦,我又来到北京,一个人,带着我刚出版的诗集。在北大西门我见到了我的师兄,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三四年后,他竟然成了我的老师,这是后话。第一次看到他,觉得他很秀气,看上去大概20出头,很年轻。原来在学校里待着能让人这么年轻!尤其是北大这样的地方,一块自由纯净的“圣地”当然能让人永葆青春。
书生气,儒雅,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成了我对北大学子一种大致的认同。
他把我带到北大食堂吃饭。北大农园。学生来来往往,我这个外地的中学生有点紧张和不自然。他倒很热情,点了一大桌子菜,红烧鱼什么的。我看着窗外的风景,北大学生,行色匆匆。
吃完饭后,他把我带到他们宿舍。那时博士生宿舍两人一问。我当时很羡慕他们,住的房子那么舒适宽敞,本科生还得六人一间,那时我就想我也要读到博士,只有一个目的,住北大博士生的宿舍!他们的那座楼叫“红楼”,房子很古朴,也很古老,有些年头了。花砖墙壁,红色古木,当时就想,住那样的房子多么幸福,用不着上铺下铺的。我正幻想着,他的室友回来了。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室友,孔庆东。孔老哥风风火火地进来,有种侠客风度。我的这位朋友说这就是我们中文系赫赫有名的博士生孔庆东,研究武侠小说的。
后来这两位师兄都成了我的老师,一个教现代诗歌,一个教明清小说。孔老师的课当然逃过,考试论文也是让北大师兄代写的,中文系的一位研究生,他当时的专业就是明清。当初经常去他们宿舍混,与他们宿舍的都很熟,代写几篇论文实在是小菜一碟。
我喜欢孔老师讲课,因为他很有激情。但我对历史不感兴趣,当初他的课没上几次,倒是记得他讲他自己的:一块香皂用半年。
四年北大,我一堂课不落的是两门课,钱理群老师的“鲁迅周作人研究”和吴晓东先生的“二十世纪外国小说经典”。这两门课我认为是当时中文系开得最好的课,它们都是在大三上半学期开设的。
钱老师讲课好是远近闻名的。他从来都是激情满腹,满头大汗地在台上将学生们引入一个激情时代,他讲课有朝气、有活力。老头儿当年都六十岁了,可仍有一种许多年轻人都已没有了的朝气。听他的钱老头开课的那个学期初,教室要换上好几次,因为学生太多了,一半的学生都拥在门外听,于是最终换成一个能容纳二百多人的大教窜,当时那是北大最大的教室了。听他的课的学生,不仅有文科系的学生,也有理科系的。我每次上他的课都坐在第一排,因为这样更容易被他营造的气氛所感染。他的幽默和诙谐给教室添了不少笑声。那时总觉得他的课太短了,45分钟,还没听就完了。
那时为了占座,也着实费了不少气力。我总是提前半小时到,生怕抢不到座位。
吴晓东先生的课与钱老的不同,尽管他是钱老的弟子。他讲课的风格更平和、儒雅一些,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内向文气不爱说话的书生。但他上课言辞的表达却是十分精辟的,我之所以喜欢听他的课就是因为他说话干净、清晰、有条理、黑白分明,从不拖泥带水,而且总能讲出许多新东西来,引发你自身的思考。他的课一点也不空洞,理论与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因此很生动,让学生自己根据他所讲的也能联系到自身的经验。这才叫言传身教。因此吴晓东便也成了我所尊敬的老师之一。当时我还喜欢搞电影研究的戴锦华教授的课,历史系朱孝远老师的课,还有中文系曹文轩等老师们的课。可能也只有在北大这样的地方才能自由逃课。李敖在《十三年和十三月》中写他考入台大历史系后,“除了每学期终了要硬着头皮敷衍一阵考试外,其他时间,我就乐得自由自在自己读书,或是跟一些好朋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坐在校园草地上,直谈到天明”。我的北大生活也是这么度过的。
我在北大当初上的是“文科实验班”,所谓的“大师班”。它的宗旨是文史哲不分家,培养未来的“大师”。因为我们中文、历史、哲学三个系的课都要学,大一大二要选很多课,大三你可以选你的专业,比如中文、历史或哲学。当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培养文科的大家!第三年的时候我选的是中文系,毕竟三者比起来,中文还是好混。我最终选定的是文学专业。班上30个人,21个选中文系,6个选历史系,3个选哲学系。由此可以对三系的热闹程度作一对比。
而21个中文系中又有18个选的是文学。由此可见文学专业还是最容易混的。我想现在大家都在安享生活,“大师”出了几?当初大家的志向可能都是想“直博”。班上30个人,24个是女生,百分之九十最后都出了国,出了国也不是学什么文学,而是计算机什么的,“大师”究竟出了几个?四年大家都是逃逃课,抄抄讲义,背背笔记,然后考试就过关了,有几个在真正地做学问?每个人都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即便是做学问,也是做死学问。我以为,中文系学问做得最好的就是钱理群了。他能把理论和激情结合起来,而他自身的人格魅力当然也是知识分子中少有的,这才是真学问。大师是培养出来的吗?大师又不是方便面,能够批量生产。
大学四年我总共选了60门课,学业压力非常大,你如果认为任何中文系的学生就是读读诗喝喝茶什么的,那你就错了。我们的压力是一般文科系的三倍!
文科实验班是1994年开设的。学校很重视,因此我们也就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各方面都有优待。首先我们不必去昌平园耗费一年。当时北大文科所有系的新生第一年都要去昌平园分校。第二,中文、历史、哲学系的图书馆大门都向我们敞开。那种优越感可以说班里每个学生都有的。刚开始很兴奋,因为一切都是新的,你并不知道你要接受怎样的考验。后来课程定下来了,一大堆,都是必修课,大家才感到大师班并不是这么好上的。好在我们可以逃课。这是大学跟中学的区别,自由些,但学业压力可能更重。
每个学期我们都有繁重的课程,而大多数的老师又都是照本宣科式地讲解。当然如果你觉得他讲得不好可以不去,但每个学期末的考试就成了学生们最头疼的问题。没有什么理解的东西,全是死记硬背。尤其对于我们中文系来讲,要想拿高分,就得拼命地背。成绩好的自然是背功高的,而且在答题时你必须与老师上课讲的一致,你若稍微有点与老师不同的看法而且把它写在考试卷上,那你就别想拿高分,甚至是及格恐怕也很困难。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