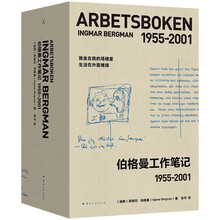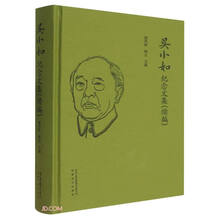一个兵和他的老婆
第一章 他说他怎样认得他的老婆
兄弟,我的为人怎样,你知道的。我只晓得有一件事干一件事,不会外想到第二件。你们叫我傻子;你们也爱我这样。你还记得我们跟曹大人打云南吗?那时我们打了一个败仗。照我们那样的军纪,兄弟,不败要算天不睁眼。我们从前线上退回来,狼狈到了家,趁势放火打劫;我们快活到了极点,百姓遭殃到了极点。我们这一营离开全师,驻在湖北河南交界的一个小镇市,叫做刘店的。镇上家家户户关了门,不关门的是穷汉。营长办公处和大半兄弟占满了那唯一的小店,只有几小棚分札在民家:我们是一个。在这儿我们等省里的命令。
那时大家都足吃足喝,不知道王法,成天给营部惹事。镇里富家的小姐和年轻媳妇,早都藏一个干净,女人的影子只有几个穷老婆儿。这扫了大家的兴。你那时顶年小,什么都要由你起头,可恶极了。那一排人,我就是爱你,兄弟;然而我真怕你,兄弟。你不懂得军法,任性胡闹,简直不分轻重:为你我常担忧,有一天你总要吃亏的。
我们借住的那家民房,在全镇最西头儿,偏僻得很,肃静得很,这我十分合意,免得在热闹地方你们瞎来。我是老实人。我真看不下你们平日的样子,所以搬来以后头一件事,便是不准你们喝酒,向东家发凶.他姓陈罢,人是上好的,县里有买卖,镇上有房产,田里有水浇地;他把老婆同女儿早就送回舅家,这办得真够我称好的,虽然这大叫你们没趣。留他一个伙计伺候我们,他自己陪你们在一个土炕上睡。我独自歇在上房,从这儿有一个小门通到后面菜园。他们房舍倒不少,搁家具的,存粮食的,马房……
你们日子过得闷闷的,好歹都不成,尤其你的火苗子按捺不下。我只装没有瞅见。
好那,有一天黄昏,我独自用完了饭,在房东的菜园里头闲溜达。我觉得无聊,这种规规矩矩的生活连我也腻烦了,干一点儿什么消遣好那?没有事。唱戏我不会;《三国演义》我没有瘾;掷骰子我讨厌:我是一个一无所能的闲光棍。头丧气的一溜烟儿跑掉,停也不停。我用手招你们回来,要问一个明白:你们早已没有影子。后来我才想出你们见我手里拿住家伙,怕来拼命。
不过这一跑倒把我弄糊涂了,马房里头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那?这尖细的哭的声音我很久就没有听见了。我怕弄错了事情。我举起六轮子,一步一步往马房里走。从这门道转过一堵另外不到人肩的矮墙,才是你们捣鬼的地方;就在这座墙头儿上,放着一盏半明不灭的洋灯。在墙尽头要拐弯的地方,我听见极细微的人的喘息。这定然是一个小孩,白天不清楚怎么开罪了你们;他的小胆一定吓破了,要不然这里不趁这个当儿逃走那?可怜的孩子!我刚转过墙,呀,我的天!呀,我的天!在我眼前那根柱子上捆着的,嘴里塞着破布的,是一个女孩子呵!她浑身一丝不挂,让皮带绑在靠里头短墙前的高柱子上,这儿原来拴马的,头发披在两肩上,散下遮住她整个的身子,头垂着,像咽了气的死人。我吓得靠在身后的墙上,移动不得: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女人,光了身子的女人,在这样破烂空房和阴暗的夜里头。我的眼睛想避开她,不成,只在她身上转着,忘记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她的奶头肥得真美,肉同雪一样,头发和老鸹一样,不像地上的人。我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过我终于瞥到了那捆得上紧的带子,从胸口到下面,连手带脚。我定过神,跑上去从后面替她解开了她的扣头,手哆嗦得要命,心不知道在腔不在腔,我用手顶住她的前胸,怕她骤然倒下去;换过手来,从她垂下的头,我取出她口里的破布。我回身褪下军氅,在我一手扶她,一手往地上铺她的时候,她的软软的面条儿身子,扑向我的怀里。
我放她在地上我的外套上面,蹲下闻了闻她鼻子还有热气,心舒展了许多。我是一个粗人。你要看见我在那儿救她的模样,不发笑才怪那。那时我自己差不多也晕了,这比杀人还难,瞅着光身子的晕了的女人。我走到门外呼了几口气,想多叫一些帮手。继而自己一思索,这反更不妙;头一桩,这事声扬出去,传到上官耳朵,于我更没有光彩,再说,它越隐秘越好,对那姑娘自然更得这样。我那时简直忘掉你们这几个浑蛋。打好了主意,我重新回到她躺的地方:她的气出入得也粗也匀了,嘴里发着像哽咽像咳嗽的声音。我不敢细瞅她,转向马槽旁边,等她活转;在它下面乱草上,我发现了一堆的女人的衣服。我拾起它们,在黄黄的灯亮里头,我辨出它们的颜色,材料和样式。这不像穷家女儿的。我走到她的身边。
她苏醒过来,在我脚下呜咽着,缩成一团,上曲住两条玉佛的细腿。我把衣服丢在她身上,不记得是否说过一句:“快穿上!”她举起头来,不哭了,翻开那样大的亮的眼睛,隔着泪水同散发,像两颗闪烁不定的猫眼睛,望定她身旁的军官。我觉得害起臊来,赶紧往外躲开,留她独自在后面穿衣裤。隔住墙我听见里头窸窸搴搴的响声,一忽儿抽噎着,一忽儿听着,这样静待了许久。这时夜里该打几更,我也不清楚。我在想着,对着门外的黑夜,活像我对着一张白纸,想着。一种奇怪的念头攒在我心上。天下再没有比我傻的。我想跑过去,跪在她面前,说我爱她,求她给我快活。我的脚同钉子一样;我的心同点着火的烧酒一样。
慢慢我从这种胡思乱想清醒过来,觉得有一团黑影要从我的眼前飞过去;我伸出手,原来抓住了她的衣襟;她打算从我手里挣扎,往外逃。我真不高兴,为什么她要怕我那?我救了她,全了她的贞节;然而她不谢我,还要从我身旁战战兢兢的偷跑。狐狸见了狼是这样;女人是这样。不,她站住了,在我的胸前定定的站住了,沉沉的瞅着我。
“老爷,你要我做什么?”
我说不出话,低下头来。
“老爷,你不放我吗?”
“我放你。”我的手松了她的胳膊,极文明的答道:“放心,在我手里,没有人敢来欺侮你。我是排长;我是君子人。他们一群浑蛋让我轰跑了,明天我得好好惩办他们一顿。解你的恨。但是我不放心,在这样深的夜里,镇上只有队里守夜的弟兄们。你逃开这儿,逃不开那儿。告诉我,你家在哪儿?”
“谢谢!”她在门前踌躇着,往黑夜望道:“谢谢。如今我不害怕了。”
“为什么?刚才——”
“刚才我怕,不过如今有你老爷——你是好人!”
我是好人。自然,我永久都是好人,至少对我老婆总是好人。她后来做了我的老婆,兄弟。那时我让她等一等,自己到屋里拾起军褂,掸去土。如果她不趁这机会溜走,一定是绝顶的傻子;然而她是傻子。我把军褂披在她身上,告诉她这可以免掉守夜的弟兄们的查问;在洋灯旁边还留下你一顶军帽,我拿起盖在她的头上。于是吹熄了灯,我随在她身后往外走着。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谁听得见谁的心跳。
围着马房前面的墙,有一垛塌下来,我们便从这儿走出去。她的脚步落得很不稳,要倒的样子。我低声吩咐她不要胆怯;她摇了摇头,那顶军帽从她蓬松的头发掉到地上。我捡起它来,趋前为她戴上,趁机擒住她的胳膊,不放回去。她靠在我的肩上,带我向大街走。我如今成了她的护卫。在一个小巷口,经了一位弟兄的盘问,我们进去了。于是又转了几个小弯,我这时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晓得快到她的家了。她忽然在一家门前立住,向我幽咽道:“假如他认出了我装的哪?那守夜的?”
我请她摸一摸我胁下的手枪。她求我把这个赏她一看,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我,说实话,没有勇气拒绝她这种要求。不过我却起了疑心,她求我的声音像打定了什么主意的样子,又哀婉,又坚决,并且亲自动手从我腰带上往外拔它。我哆嗦了。我问她干什么。她不做声,和盘在空里的鹰一样来刁抢它。我按住她一双竭了力的小手。她低下头用牙咬我的手背,这却出乎我的意外,并且她那样用力发狠,手背上的皮疼着。破开,流出血来。我说不要糊涂,人命不是儿戏的,并且这有什么用那?她扑在我怀里哭了,说她不敢进家的门。她不在外头死,进家也得死,因为她做姑娘的身子让生人看见了。我劝她想开些,看见身子同失掉身子完全是两件事情,回家把苦诉给爹娘,老人们总该体恤的,要不然我陪她进家,给爹娘做证人,老人们非特不责备,恐怕还要疼惜一个不了。
“疼我?妈也许;不过妈是爹的人。家里没有谁疼我;从前有姆,可惜死了。而且,老爷,后天我就要出嫁。”
“小姐,那你更该回去;”我吃惊着:“他们丢了你一定万分着急。”
“噢,别逼我回去!让我死罢!让我死罢!别让我嫁给那样的人家!我恨他们!那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死罢!”
我现在没有法子再劝了,并且,你爱的人在你胸前绝望的号啕着,哀告着,铁石心肠真是也得软化。但是我自己又没有地方送她过夜,为难之极。我问她有什么近处可以投奔。她摇着头,呜咽着。我问这儿是不是她家,她哭得更利害。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拉着她的左胳膊,就往石阶上扯;她抗拒着,缩住步,随后发出一声极长的叹息,向我表示顺服道:
“老爷,你——为什么——要——要救我,那时死了,也比后天活着强——老爷!”
我立刻觉出自己做得太过火,女人的委屈男子不容易体贴出的。为什么我要逼她嫁那她不认识不爱的人?这和让人强奸死有什么分别?而且我真恨这两扇门,和棺材盖似的,分纹儿不动,里头静静的,仿佛丢了姑娘和死了猫狗一样。我不倔强了,晕头晕脑的向她要主意。她轻轻的扑哧笑了。笑什么?她说她忍不住笑,因为我的傻,因为她晓得我要屈服的。我们臂靠臂,向前缓缓走去,又转了一条小巷。我们都不清楚往哪儿走,走到哪儿为止。我觉得我又年轻了,和在妈跟前一样。我搀着老人家跌跌打打,往爹的坟头去。一样的夜晚,不过如今我身旁换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带着和我一样的年轻的心。她问我为什么掉眼泪。
“小姐,在你身边,我不由得想到从前我的母亲。”
“停住!我也正在想——你还是送我回家去罢。噢,妈妈!不过——不过——好,走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