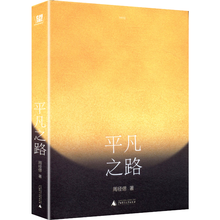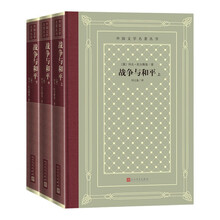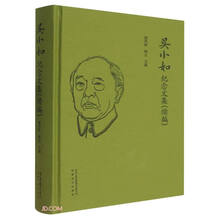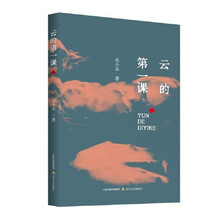狗儿爷 咱的地没啦,爹!那不是我的酒。是他的——李万江的酒,他提来的,满满儿一壶。李村长是好人,是恩人,给咱这么大脸,不能不喝。他一杯,我一杯,我一杯,他一杯,小酒壶一打跟头,酒净了,人醉了,就都没了!不是没了——李村长说——乡长指示,咱村要“一片红”,人家都红了,他狗儿爷不能当“黑膏药”!不当,打仗支前,土改分田,咱没落(读Ia)过后——我说——可是,把那人马土地,说声归,就归了大堆堆儿,你一人浑身是铁捻多少钉?一人指挥几百条锄把子,能行?别忘了,亲哥儿俩为一垄青苗,还打出花红脑子来呢!可是行呗——他说——你就赌好儿吧,傻老爷们儿,眨眼之间,咱就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饼干。我说:我不情愿。他说:你就是财黑子,地虫子,三斧劈不开的死榆木头,脑袋瓜子赛石头。我急了:当“黑膏药”,俺认了。他说:那就揭“膏药”!我问:怎么个“揭”法?他说:把你新买的“大斜角”,还有(指脚下)这坟地葫芦嘴儿,都拢过来,划出那边边沿沿、零零星星的来跟你换,是膏药也贴在脚指头上,不能胸脯上来块黑。——别蒙我啦,谁不知道“远女儿近地无价之宝”啊!再说那都是薄碱沙洼,种一斗,收八升,不换!——不换就得归堆儿,一片红,乡里还等着报喜哪,来,喝!——喝!这工夫,我媳妇,小金花插嘴啦:逢自庄稼主儿过日子,就得随个大溜儿,图个顺气,人家都那样,独独儿咱来个花“虎拨拉”(一种灰绿色鸟)——个色!人家万江兄弟没日没夜地跑动是为谁,还不是为咱好?丑话说前头,你要不入,咱就分家,虎儿俺们娘儿俩入,俺们可不跟着你当那个“膏药”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