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
梦境
你说你从19岁开始一直做一个梦。梦里你呆在一个白色的房子里,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抽屉,和一只水壶。你在房间里一直找东西。我觉得那像我玩儿过的一种游戏,它不计时间,把你放在一个房间里,我曾经在地毯下面找到一把钥匙,有了钥匙我欣喜若狂,可是让人恼怒的事情立即发生了,我不但要找到钥匙,更要找到的是那把锁。窗子紧闭,没有门。你口述中的梦境让我再次记起了那个糟糕的游戏,因为找东西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刚开始你连续做这个梦的时候你还很抓狂,可是越久你越有耐性,你不停地翻找,不停地打开再关上那个抽屉,你检查了床甚至搬开它,检查四条腿的下面是否压着什么宝贝。我问过你,你觉得这个梦给你带来了什么。你看着我的眼睛,慢慢地说:“当我看见你第一眼时,我注意到你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我觉得可能我要找的就是它。”我怔在那里,希望这只是你接近我的一个借口。
紧紧发条
我戴着旧的珍珠项链,穿着阔脚裤蹲在公司楼下的木长椅上,我实在是头疼,我总感觉把自己放置在高处然后蜷缩起身子,抱住小腿我就会舒服。我的头像被除草机舔过了一样。你在我旁边走过,我看见你的牛仔裤还有帆布鞋。周围的环境都太安详,你也是安详的装束。我实在无力抬头看你到底长得如何,我觉得我被整个城市抛弃,陷入孤独的疼痛中。谁知你坐定在我身边,撑开一本书,读了起来。
我的头嗡地响了一下,你那么不和谐地出现在我的病痛面前,我决定离开这里。我把脚装进鞋里,穿鞋的过程很快,我不敢低头看脚,后来凭借直觉我穿好鞋,走。
你叫住我,站在我面前。你比我高20cm,你有189cm。我眼睛晕忽忽地平视着你的胸膛,我也不敢抬头。
你弓了膝,俯下身子抬着头看着我,和我的眼睛在一条水平线上。我哇地叫了出来,你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你鞋穿反了……”你说。
“我乐意!我乐意反着穿。现在墨尔本和尼日利亚都流行这个穿法,你管得着嘛?这么多人的场合你捂住我嘴你想干嘛啊你?!”我说话声音特别大,我是被吓坏了,我越受惊吓越聪明,而且我是学地理专业的,我背地名就像说相声的报菜名一样伶俐。
“啊……”你很尴尬站在那儿。
“没事儿的话本小姐就告辞了。”那时我脑袋已经不疼了,原来惊吓可以治疗我的偏头疼。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你一直都记得怎么来帮助我摆脱病痛。那就是吓唬。
你吃掉了我的左边乳房
你有好多名字,都是我给你起的。八格、洞洞、太空飞船、马保酒、卡罗斯、披头士不相信老鹰、灰裤子、方庄的眼泪、芥末酱男人……你赞叹我起名字的能力,你说我是骗子和乌鸦嘴,还说我就会给人起外号,而且我就是个不靠谱儿的女人
那天的相遇实在太美好,其实我的鞋就是穿反了,你被我的伶牙俐齿搞晕掉了。我看你可怜,就让你随我坐回到长椅边上。这时我看清了你的长相。你一定刚刮完胡须,因为下巴有些红肿。你的头发很短,眼睛清澈。穿着双排扣的灰色呢子短夹克。我们并列坐在长椅上,脚挨着脚。我仍旧不低头,脑袋不带转动,看着前方,和你对话。此时我知道,我要变得温柔一些,像个女孩子,不要把你吓跑。
“刚才对不起,我又在狡辩。”我温柔的声音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啊……你……真聪明哈。”你的声音都热热的。
“我……我学地理的,就擅长背地名。所有我解决不掉的尴尬时刻,我全都套用地理手段去解决。比如我曾经在一个摇滚PAR上拒绝一个搭讪的外国男人,之间我使用过7个国家名字,为了告诉他我是个国际女友,我的男朋友遍部世界各大洲,所以见多了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他结果被我吓跑了。你看,我是很无辜的。”我一激动脑袋又不疼了,我说完这些话我就后悔了,我扭过头看他的反应,我已经尴尬得要死了。
“你现在好点儿了吗?”
“好像好了一点儿,可还是不敢低头,我就是因为在办公室里无聊了低头看蚂蚁搬家,看着看着就头疼起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只要低头还是会头疼。”
“你把鞋脱在地上,我给你换好位置,你再穿。”他是个好男人,百里挑一的。我照他说的做了,穿着正确的鞋子,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被覆盖掉的寂寞
你叫马奇,我叫杨绝色。你25岁半,我23岁半。你吃饭时喜欢喝汤,我吃饭时喜欢喝酒。你坐在我身后看报纸,我坐在梳妆镜前看着你阅读时的表情。你在看到战争时皱了眉头,你在看到社会案件的时候又皱了皱眉头,你在看到我的专栏文章时终于笑了起来。你的笑还是不动声色的,安静的,像被人往心上洒了白糖一样。那天我写的专栏文章题目叫作《野合有多野》。我在文章开始记叙了一段我们在阳台上做爱的情形,后来我又分析了城市里适合野合的几个去处,以及性爱的突发性。随时随地会发生的行为绝对是有危险的,比如被偷窥或者是一方太过紧张激动而脑溢血死亡等等。最后话题转到宣扬健康性爱,然后我批评了我们在阳台上做爱,因为天气太冷,我们被冻僵了,完全没能体会那种神奇的时刻。而且当时阳台的围栏上落下了一只鸟,我全力以赴地观察那只鸟,而那只鸟也在全力以赴地观察我们俩,最后变成三方对视的局面。等鸟飞走了,茶也彻底凉了。我们收工回房时,打开暖风,穿着衣服就跳进了被窝。哇,因为这个而被冻死也不值得……
你笑着看完我的口水专栏,然后把报纸合上,抬头看着镜子里的我,我们在反射中对望。刚要酥软地跌进你怀里的时候有人敲门。
还是老规矩,来外人,我不做声,你关上卧室的门去客厅解决掉麻烦,然后就没有外人知道我们同居的事情。
我坐在房间等你回来,可是等了很久,直到我觉察出了问题。
晚归的芥末酱男人
这是你父母单位宿舍,大学的家属院住着一些古怪的人,在我看来,和他们沟通比什么都难。学究和文痞,两者我都崇敬。可是最怕的是这个时代孕育着一大堆介于二者间的教授们。他们不中不西,还爱讲别人的家务事。我虽然没和他们接触过,可是通过他们的眼神我就确定他们有着这样的气质。你没阻挠过我对任何人的判断,你总是笑。马奇,你知道么?你的笑实在太温暖了,太像太阳或者月亮了。
那天你被神秘的敲门声叫走。卧室门被你带上。我坐在梳妆台前等你回来,对着镜子看着那扇门,当时我还找到了一个很酷的姿势,希望你一进来看到我的模样就把我搂进怀里亲上一亲。我保持那个姿势保持了很久,直到睡着了。
后来天黑了,我醒了,我看见窗外的黄色路灯斜射到地板和桌子上,没有一点声响。我害怕了。我的头又开始疼。我突然想到你被敲门声带走后就再也没回来,我就哭了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冲出卧室,客厅里也很黑。我打开灯,吓了一个踉跄,一个很丑的脸上充满刀疤的男人坐在饭桌旁的凳子上。我尖叫起来,低头看了看他的鞋,就是那天我见你时你穿的那双黑色帆布鞋,上面有瑞士国旗形状的图案。我因为低头又因为惊吓,晕倒了。
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因为惊恐我迅速苏醒。我观察眼前的一切,我并没有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所以我发现这不过是个梦。而眼前的一切都和梦里梦到的一样,我摆姿势等你回来而在梳妆镜前睡着。我擦掉脸上的汗和眼角被梦吓出的泪水,极力反省到底是梦还是真的,到底哪个才是最真的时空状态。我希望那个饭桌旁和你穿一样鞋子的刀疤男人是梦里的东西。可我又害怕是什么特异功能,让我感觉到了未来。我害怕现在打开卧室门,看到真的有那么一个男人坐在那里,他和你交换了鞋子,而你却不见了。
我被这一切吓得直打寒战。我把手腕上的传家的龙凤镯子放在嘴前亲吻,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要它给我力量,我想立即死去或者是见到你。我不要这么孤单地被梦缠绕住,或者是被这种奇怪的事件纠缠住。我只要你拉着我的手走在林荫路里,后来我们走过那段路。太阳出现了,照在我们的脸上,你低下头吻了我。我穿低领的衣服,露出一段锁骨。那一切该多么美好。我不要现在这样。我害怕。
在我不敢哭泣还在拼命流泪的时候,电话铃突兀地响起。电话机就在我不远处的地方,我快速走到沙发里,陷进去,让自己感觉很安全,然后拿起听筒。这样刺耳的铃声,在我不确定客厅是否坐着刀疤男人的时候,我希望它从来没响起过。我拿起电话都不敢喂一声。
是你的声音,我的听力忽然也下降了,在你的语言词汇中寻找和你我有关的点。当我捕捉到你安好无事只是去了一趟邻居家之后,我歇斯底里放声哭泣。我太害怕了,而又在自己的脆弱和混乱敏感中,隐约查觉到,自己大概是一名精神病人,我的精神有问题。我害怕一切疾病。而精神疾病又是我自己完全不能调节的,它是掌控我一切行为的龙头。如果他脱扣再也拧不严实了,那我就会像疯子一样在街道上扭屁股或者是在房间里拿着剪刀到处欺负人……我越想越怕,哭声估计搅乱了大学周围的所有人们。
你拿着乐谱跑进房间里来,焦急地站在我面前抱住我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我仍旧手握电话筒大声地哭。你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只是心疼地抱住我,亲我的头发。你太高了,你的身子弓了好久,现在这么想起来,那天你肯定是很累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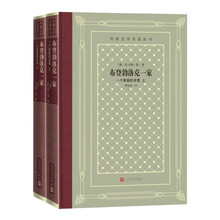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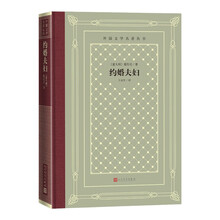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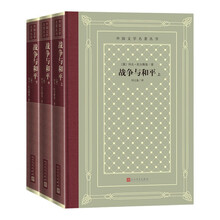



——塞宁
忽然消失的夏天,那个季节,如同一张打了孔,布满了裂纹的CD,在心里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不停旋转,播放着无数破碎的声音。
——王小泉
我想说的,十分简单而可笑,可能只为了掩饰自己的没落,粉饰脸上虚情假意的笑容,有时单纯幼稚得如同夏日里失落一地的阳光碎屑,明明掉落却真实而空虚。
——商夏周
她的声音干燥温暖,穿梭在众多嘈杂的响动里,然后又准确传入我的耳膜,于是那些话语幻化成为过去的画面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那还是十几岁年轻的他们,却在那时起就承载了十几年的时光。
——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