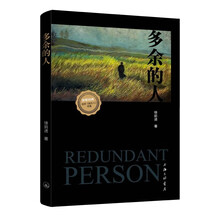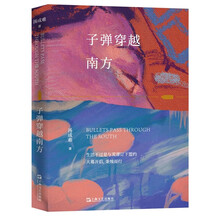大牛低下头,讪笑着。他心里说,你这贱货,千人压万人日的贱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只不会下蛋的母鸡。
少东家也冷言冷语说:“吃亏了吧,往后少跟人发横。”
大牛还是讪笑着,在心里说,你算什么东西,不就是脸白些个,脸白又管啥,别以为我不知道,大奶奶在炕上骂你没用。
大奶奶又问二傻:“那马五,他是哪地界的人?”
二傻说:“羊、羊、羊……”
大奶奶烦了。“傻东西,整天就知道羊,回你的羊圈去。”
二傻回了羊圈,羊群见到他咩咩地叫,挨着他腿边擦痒。二傻把羊推开,他心里有些委屈。他想回大奶奶的话,只是在大奶奶面前,他说话就觉着不顺畅,堵在嘴边吐不出来。他本想告诉大奶奶,马五不是哪地界的人,马五是羊投胎的,只有羊才吃兰花花,才把花辦咬得咔嚓咔嚓响。二傻不是羊投胎的,可他知道自己下辈子会转世做羊,所以马五才管他叫兄弟。没人叫二傻兄弟,只有马五。
八月秋凉,北边刮过来的风里带来了寒意。五马河不再发出欢快的淌水声,在有些浅滩处,把裤筒卷到膝上就能过河。那是呼家圩长工最忙最苦的时节。高粱熟了,一颗颗高梁米鼓得要炸开,沉甸甸的穗头压得基秆腰弯腿软。大奶奶站在炮楼上向圩外望,四下都是艳红,一直连到天边,乍看着就好像雨前的火烧云。她把长工们赶到高粱地里,吃喝拉睡都不让回家。那时节也苦了大奶奶,她不干活,可把嗓门吆喝哑了。
长工们累得像高粱秆,腰腿都直不起来。他们在密密的高粱地里,活尸一样地挪着脚步,他们身上显着有劲的地方,就剩下了两片嘴唇。那两片嘴唇不停地翕动,见啥咒啥。他们咒九月天,咒高粱地,咒大奶奶催命般的吆喝,咒少东家的清闲。他们也咒自己,咒自己命苦。还咒土匪,要不是怕土匪烧粮,长工们本不必这么没日没夜地干。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