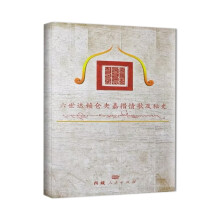斑点带子案
八年来,我一直潜心研究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推理思路,先后记录了七十多个案例。翻阅一下这些案例记录,我发现许多案例都以悲剧告终,当然也有一些皆大欢喜。但是大部分案例都是离奇古怪匪夷所思,这中间没有一例是平淡无奇的。这是因为,他做侦探工作与其说是为了赚钱,还不如说是出于对侦探专业的爱好。他只接受那些独特甚至是近乎荒诞无稽的案件,对普通的案子从来不屑一顾,也不多参与任何调查。在这些变化多端的案件中,我想不起有哪一例会比萨里郡罗伊洛特家族案件更具特色。这件事,发生在我和福尔摩斯交往的早期。那时,我们都是单身汉,在贝克街合住一套公寓。本来我早就可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但是,当时我曾做出严守秘密的保证,直至上月,我为之做出过保证的那位女士不幸逝世,这才解除了这种承诺。现在,是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因为我知道,舆论对于格里姆斯比,罗伊洛特医生之死众说纷纭,广泛流传着各种谣言。这些谣言使这件事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加骇人听闻。
事情发生在1883年4月初。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穿得整整齐齐,站在我的床边。他是一个爱睡懒觉的人。而壁炉架上的时钟,才刚七点一刻,我有些诧异地朝他眨了眨眼睛,心想这么早叫醒我干什么呢?因为我的生活习惯是很有规律的。
“对不起,把你叫醒了,华生,”他说,“但是,你我今天早上都不能睡懒觉,先是赫德森太太被敲门声吵醒,接着她报复似的来吵醒我,现在是我来把你叫醒。”
“那么,什么事——着火了吗?”
“不,是一位委托人。好像是一位年轻的女士来临,她情绪相当激动,坚持非要见我不可。现在她正在起居室里等候。你瞧,如果一位年轻的女士一清早就把还在梦乡的人吵醒,我认为她定有紧急的事情,她不得不找人商量。假如这是一件有趣的案子,那么,你一定希望从一开始就能有所了解。所以,我无论如何应该把你叫醒,给你这个机会。”
“我的老兄,那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失掉这个机会的。”
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观察福尔摩斯进行专业性的调查工作,欣赏他迅速地做出推论。他推论之敏捷,犹如单凭直觉做出的,但总是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我匆匆穿上衣服,几分钟后准备就绪,随同我的朋友来到楼下的起居室。
一位女士端坐窗前,她身穿黑色衣服,蒙着厚厚的面纱。她在我们走进房间时站起身来。
“早上好,小姐,”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我的名字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挚友和伙伴华生医生。在他面前。你可以像在我面前一样谈话,不必顾虑。哈!赫德森太太想得很周到,她已经烧旺了壁炉。请凑近炉火坐坐,我叫人给你端一杯热咖啡,我看你在发抖。”
“我不是因为冷才发抖的。”那个女人低声说,同时,她按照福尔摩斯的请求换了个座位。
“那么,是为什么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是因为害怕。”她一边说着,一边掀起了面纱,看得出,她确实是处于万分焦虑之中,样子很令人怜惜。她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双眸惊惶不安,酷似一头被追逐的动物的眼睛。她的身材相貌是三十来岁的模样,可是头发却夹杂着几缕银丝,一副未老先衰萎靡憔悴的模样。歇洛克·福尔摩斯迅速地从上到下打量了她一下。
“你不必害怕。”他探身向前,轻轻地拍拍她的手臂,安慰她说,“我们很快就会把事情处理好的。我知道,你是今天早上坐火车来的。”
“这么说,你认识我?”
“不,我注意到你左手的手套里有一张回程车票的后半截。你一定是很早就动身的,而且在到达车站之前,还乘坐单马车在崎岖的泥泞道路上行驶了一段漫长的路程。”
这位女士猛地吃了一惊,惶惑地凝视着福尔摩斯。
“这里面没什么奥妙,亲爱的小姐,”福尔摩斯笑了笑说,“你外套的左臂上,至少有七处溅上了泥。这些泥迹都是新沾上的。除了单马车以外,没有其他车辆会这样甩起泥巴来,并且你只有坐在车夫左面才会溅到泥的。”
“不管你是怎么判断出来的,你说得完全正确,”她说,“我六点钟前离家上路,六点二十到达莱瑟黑德,然后乘坐开往滑铁卢的第一班火车。先生,这么紧张我再也受不了啦,这样下去我会发疯的。我是求助无门——一个能帮忙的人也没有,除了那么一个人关心我,可是他这可怜的人儿,也是爱莫能助。我听人说起过你,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从法林托歇太太那儿听说你曾经帮助过她。我正是从她那儿打听到你的地址的。噢,先生,你是否也可以帮帮我的忙?至少可以让我拔出泥潭,给我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吧。但是目前付不起酬金,但在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以内,我即将结婚,那时我就能支配自己的收入,到时再把线付给你,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福尔摩斯转身走向他的办公桌,打开抽屉的锁,从中取出一本小小的案例簿,翻阅了一下。
“法林托歇,”他说,“啊,是的,我想起了那个案子。是一件‘猫儿眼宝石头饰案’。华生,那还是你来以前的事呢。小姐。我很乐于为你这个案子效劳,就像我曾经为你的朋友效劳一样。至于酬金,我的职业本身就是它的酬金;当然,你可以在方便的时候,支付我在这个案件上所花的费用。那么,现在请你把一切告诉我们吧。”
“唉,”这位女士回答说,“我很焦虑,但我对我所担心的东西十分模糊,我的疑虑完全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引起的。这些小事在别人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所有的人都把我说的这件事看做是一个神经质女人的胡思乱想。包括我认为最应该帮助我的那个人,他当然没有这么说,但是,我能从他安慰我的言词和回避的眼神中觉察出来。我听说,福尔摩斯先生,你能看透人们心中的种种邪恶。请你告诉我,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你慢慢讲吧,小姐。”
“我的名字叫海伦·斯托纳,我和我的继父住在一起,他是位于萨里郡西部边界的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家族——英国最古老的撒克逊家族之一——的最后的一个活着的人。”
福尔摩斯点点头, “这个名字我很熟悉。”
“这个家族一度是英伦岛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它的产业占地极广,超出了本郡的边界,北至伯克郡,西至汉普郡。可是到了上个世纪,连续四代人都好逸恶劳,荒淫浪荡,挥霍无度,到了摄政时期终于被一个嗜赌成性的浪子搞得倾家荡产。除了几亩土地和一座二百年的古老宅邸外,其他财产都已荡然无存,而那座宅邸也已典押得差不多了。最后的一位地主在那里苟延残喘地过着落魄王孙的可悲生活。但是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继父,意识到他必须认清这种新的景况,他从一位亲戚那里借到一笔钱,这笔钱使他得到了一个医学学位,并且出国到了加尔各答行医。在那儿凭借他的医术和坚强的个性,业务非常发达。可是,由于家里几次被盗,他在盛怒之下,殴打当地的管家致死。差一点被判处死刑。就这样,他遭到长期监禁。后来,他返回英国。变成一个性格暴躁、失意潦倒的人。
“罗伊洛特医生在印度时娶了我的母亲。她当时是孟加拉炮兵司令斯托纳少将的年轻遗孀,斯托纳太太。我和我的姐姐朱莉娅是孪生姐妹。我母亲再婚的时候,我们年仅两岁。她有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每年的进项不少于一千英镑。我们和罗伊洛特医生住在一起时。她就立下遗嘱把财产全部遗赠给他,但附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在我们结婚后,每年要拨给我们一定数目的生活费。我们返回英伦不久,我们的母亲就去世了。她是八年前在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的。在这之后,罗伊洛特医生放弃了重新在伦敦开业的打算,带我们一起到斯托克莫兰祖先留下的古老宅邸里过活。我母亲遗留的钱足够支付我们的一切生活费用,看起来我们的幸福生活似乎是毫无问题的了。
“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里,继父发生了可怕的变化。起初,邻居们看到斯托克莫兰的罗伊洛特的后裔回到这古老家族的宅邸,都十分高兴。可是他根本不和邻居们互相往来,更别说交朋友。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深居简出,不管碰到什么人,都穷凶极恶地与之争吵。这种近乎癫狂的暴戾脾气,在这个家族中是有遗传性的。我的继父可能是由于长期旅居于热带地方,致使这种脾气变本加厉。于是,一系列使人丢脸的争吵发生了。其中两次,一直吵到违警罪法庭才算罢休。结果,他成了村民们望而生畏的人。人们对他敬而远之,因为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人,他发怒的时候,简直是什么人也控制不了他。
“上星期他把村里的铁匠从栏杆上扔进了小河,我花了很多钱才避免了又一次当众出丑。除了那些到处流浪的吉卜赛人以外,他没有任何朋友。他允许那些流浪者在那块象征着家族地位的荆棘丛生的土地上扎营。他有时候会到他们的帐篷里去,接受他们的殷勤款待。有时候他还会随同他们出去流浪,长达数周之久。他还对印度的动物有着强烈的爱好。这些动物是一个记者送给他的。目前,他有一只印度猎豹和一只狒狒,这两只动物就在他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村里人就像害怕它们的主人一样害怕它们。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