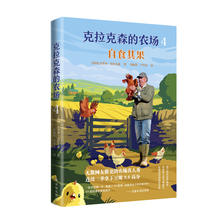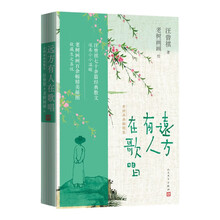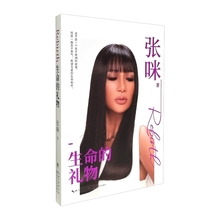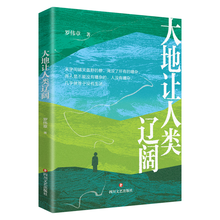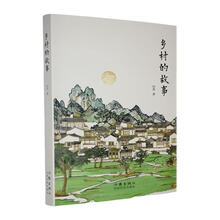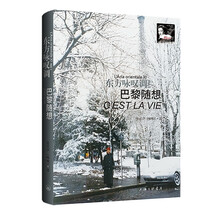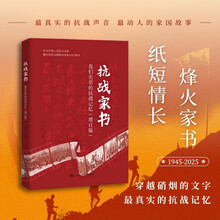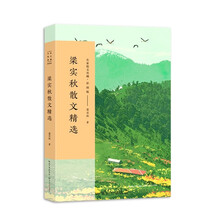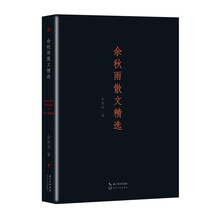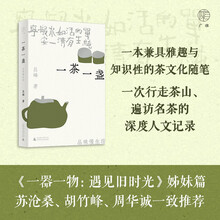小说
一我和小说
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小说写作之后,我仍然是个业余作家,这里面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比如在我们中国,作家这个行当似乎从没有职业化,我们有的只是专业作家,几乎没有职业作家。而在绝大多数国家里,作家这个行当都是高度职业化的,至少是半职业化的(有相当多的重要作家在大学里任职——驻校作家或教创作的教师),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的国家、民族以及使用相同语言的读者担负的全部责任就是写出作品。
大概也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进入专业作家行列的幸运,我可以相对自由地运用我的智能。我对我写小说这个事实颇感骄傲,因为我喜欢这个行当,也自想有这方面的禀赋;我可以不必为了所说的职业道德方面的考虑修正自己,因为我只是个业余作家,我没拿别的专业作家在职务上拿的那份官俸。这并非意味着通常理解的自由,一个作家不可能享有绝对意义的自由,大多数作家也不会要求绝对自由。读过我作品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个离时事政治很近的作家,但我确切地相信,一个出色的作家的基本点不会与他的国家以及他的民族的基本点相悖。同样道理,他的出发点不会只服从于应和,包括仅仅应和他的国家他的民族的政治需要和利益,也因为可以不必应和,一个作家才可能充分运用自己的智能去思考和写作,作最大限度的发挥,以达到最佳效果。
长时间业余状态,持续的热爱和专注,使我在这个世界上只对这一件事着迷,我的全部生活(包括家庭生活)的重心也都在这一件事上面,全部与此有关的方面也是我唯一的津津乐道的话题。换一种说法,还在我是个业余作家的时候,我早就进入了典型的职业心态,我不是专业作家却是个职业作家。不是很怪吗?应该也很有趣。
我自以为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对小说这东西非常熟悉,我有我的价值判断尺度,有我的极端个人化的想法。许多搞小说的人改行干别的去了。这个世界提供的可能性太多,不只有小说才更有干头儿,只是我有点执迷不悟。由于我的一些极端个人化的想法,我受到称赞,许多读者喜欢读我的小说。同样由于我的另一些极端个人化的想法,我被指责,成了文学的罪犯,有趣的是在我被更多的读者喜欢和接受时发生了这种不幸。说我堕落为通俗小说写家,说我艺术生命早衰,也如我的朋友北岛曾经有过的遭遇,马原由单个的人忽然成了复数,成了马原们。
到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是我还是我的批评人?我虽然也被误解甚至也被伤害过,但我不相信其中会有非学术方面的原因,我坚信是对小说本身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二小说外表
小说的概念越来越不容易界定了。部分原因是文无定法这条古老原则的持续作用,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二十世纪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潮的变化更迭。先是时序规则被发现是个骗局,接着摧毁的是情节和故事,小说变成了一种叫人云里雾里的东西,玄深莫测,不知所以。一批创造了这种文字的人成了小说大师,被整个世界的小说家尊为圣贤,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芙,乌纳穆诺,莫名其妙。
如果把这个范围拓得更大一点,我还要提几位我所尊敬的人如卡夫卡、福克纳和用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贝克特。
这里不回顾小说的历史。但凡对二十世纪小说价值演变有兴趣的人都看到某种契机,化用汉人一句古老的箴言最恰切不过——天变道亦不变。以为精神分析学是向前进了,以为打破时空观念是向前进了,以为采用意识流手法是向前进了,结果呢?小说成了需要连篇累牍的注释的著述,需要开设专门学科由专家学者们组成班子研究讲授,小说家本人则成了玄学家,成了要人膜拜的偶像。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