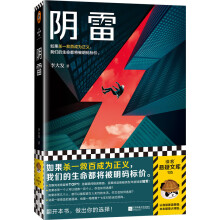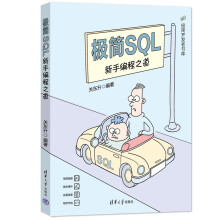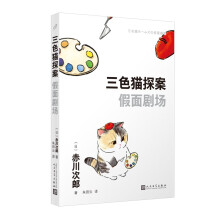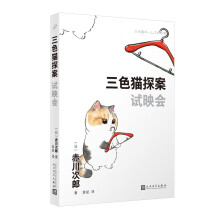鲁迅与广告
把鲁迅这个名字与广告扯到一起似乎有点不伦不类,甚或有几分亵渎,因为人们对广告多的是厌烦,少的是好感。都说现而今是信息时代,而最富侵略性的信息,恐怕首推广告,因为它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而那内容又皆咄咄逼人,足以“振聋发聩”,或是极尽挑逗之能事,隐然有你若不受招徕便要追悔终身之意。以我们对广告如此恶劣的印象,实在难以想象鲁迅与广告会有何瓜葛。
不过鲁迅的确草拟过不少广告,《鲁迅全集》中收录的就不下十数条,而广告的确也有不自吹自擂、据实道来的。
登在《京报副刊》上的《苦闷的象征》广告文日:“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鲁迅告白。”这里毫无渲染,且特别声明书的性质,“其实”二字下得尤妙,犹云:“书中并无‘性苦闷’之类,对某类书有特别兴趣之读者诸君幸勿误会。”搁在今日某些书商、出版社手里,那书名正可利用或是正希望其能有误导之效的,做此声明,岂非自断财路?
不妨拿近年某出版社所出林语堂《红牡丹》一书做个对照,那上面的广告语赫然写着“性的冲动,情的需求,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这已是堕入地道的“瞒与骗”了,我们通常所见的广告虽不致如此,然而夸大其词却是不免的,而说大话、唱高调,里面有意无意间实在也就含了“瞒与骗”的成分。鲁迅一生最反对瞒与骗,反对假大空,此种精神甚至也具体而微地体现在他拟的广告上。最好的例子是他为《莽原》重拟广告一事。
1925年,《京报》主持人邵飘萍与鲁迅商定出《莽原》周刊,随《京报》附送。邵飘萍遂拟了一条广告登在报纸广告栏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消息:如何改造青年的思想?请自本星期五起快读鲁迅先生主撰的《××》周刊,详情明日宣布。本社特白。”头一句即拉开架式,先声夺人;第二句问来亦是动人听闻,后面隐去刊名,则是故弄玄虚,设置悬念~广告的种种招数都用上了,似乎也并无大错。不道鲁迅看后大不悦,斥为“夸大可笑”,遂以第三者口气重拟一条,并“硬令登载”,且“不许改动”。于是第二天的《京报》上又出现了一则广告,云新出周刊一种,“是为《莽原》。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但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云。鲁迅先生编辑,于本星期五出版。”——恳挚实在,诙谐风趣,与邵的夸张招摇恰好相映成趣。
但是事情还没完。邵飘萍虽因“硬令”,只好刊出,内心却大约觉着太不像广告,故又在广告之后加了几句“无聊的案语”日:“上广告中有一二语带滑稽,因系原样,本报记者不便僭易,读者勿以辞害志可也。”鲁迅看了哭笑不得,给许广平的信中叹道:“做事遇着隔膜者,真是连小事情也碰头。”
鲁迅多半是要碰头的,因为他与“广告界”的精神实在大异其趣。广告的本意大约不过是广而告之,据此,广告的要求应是准确地传递出某种信息,而商家做广告意不在此,要的是“轰动效应”,是轰动带来的经济效益。依照前者,鲁迅的广告可得满分;依照后者,则恐怕要判不及格了。
当然鲁迅的广告还不止于据实相告,字里行间有调侃、有讥嘲,诸如“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之类的“滑稽”语,并非有意滑稽,亦非刻意摆出低姿态,而是暗有所指,比如这里就是和夸饰的作风唱对台戏,给邵飘萍们一点难看(邵飘萍应是同一战壕中人,后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但以其趣味而言,实与鲁迅相去太远)。这就传出广告以外的信息了。难怪未与鲁迅反目之前的高长虹,看了未名社出版物后面的广告后,道是“普通的批评看去像广告,这里的广告却像是批评”,赞其“别开生面”了。所谓批评像广告,乃是那时的评论与今日的情形相仿佛,多有标榜吹捧之嫌;至于广告像批评,看鲁迅拟的广告便知。
我估猜高长虹看到的是一则题作“《未名丛刊》是什么,要怎样?”的广告。里面如此这般地写道:
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的意思,乃是还未想定题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它了。
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书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
写这广告时鲁迅与胡适为首的一群名流学者已然分道扬镳,胡适等人开国学书目、青年必读书,已被目为或是自许为青年导师。明乎此,则所谓“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国民非看不可”之类的反语,其批评锋芒指向阿处,自是一目了然。
鲁迅确实是一位斗士、一个性格鲜明的人,他在回忆性的散文中固然时而借题发挥,对目下的人事旁敲侧击,甚至在广告中亦表达出自己的好恶,不忘对“学者们”“好的世界”施以一击。现代著名作家中许多人因为办书店、编刊物、出书,都曾写过广告,如茅盾、林语堂、叶圣陶等。因是文人,笔下自然另成一格,与寻常广告大异其趣。不过鲁迅仍旧显得特别,不必问谁是作者,单看这峭拔的文风,看看里面的反语我们便知道,是鲁迅的手笔无疑了。
鲁迅的书账
鲁迅的论敌常对他有些恶形恶状的描绘,有夸张他被香烟熏黄的牙齿的,有想象他的“醉眼蒙咙”的,又是烟,又是酒,撇开背景不论,单从这些字面上去看,鲁迅倒真像是“失意文人”,或是像个名士了。实则鲁迅最是个认真不苟的人,即在生活小节上也绝无文人习气。常到鲁迅家走动的郁达夫发现他的书房里总是整整齐齐,书案上亦井然有序,且一尘不染。这真让郁达夫这个地道的名士派大为讶异了,因为他所知道的一些文人,书房总是凌乱不堪的。鲁迅的不苟从他的日记上也可见出。他的日记并不像今日某出版社推出的《名人日记》之类,里面到处是“思想火花”和滔滔议论,而是地道的流水账,简而又简,但他每日必记,从1913年起,到1936年去世,几乎没有一天拉下。偶尔有几天漏记,也必要说明“失记”。既是仅限于记事,有时无事可记,记什么呢?记得最简的是只有天气,阴晴雨雪。我有位同窗曾细读鲁迅日记,告我他发现日记中常见“濯足”、“夜濯足”字样,而且有好多日日记里只有这两三字。回想一下,恍惚也有这样的记忆。这当然不是“濯足长江万里流”的濯足,不过是在脚盆里洗脚罢了。想来鲁迅每日伏案到深夜,脚已冰凉,暖水温泡,甚是惬意,故尔常有此一记吧?据此也可推知鲁迅的日记多是次日记的,濯足完毕当从速就寝,不见得再去握管了。
不过鲁迅日记里记得最认真详尽、最清楚明白,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要算他的书账。鲁迅有一习惯,每购一书,不仅在那一日记下书名,而且也记下书价,而且巨细无遗,毫厘不爽。比如《仇十洲麻姑仙图》等图,每枚价仅八分,也都一一记录在案。1913年5月买的一册《观无量寿佛经图赞》所记价为0.312元,更是精确到厘了(可知那时买书的讲价是极细的,但不知几厘几厘是如何找法)。每年岁末,鲁迅照例要算一回总账,将所置书籍、图册、拓片等按购置的时间顺序一一列出,月为单位是小结,最后算清一年共花费几何,此外又还常算出平均每月花去多少。
鲁迅自奉甚俭,衣的朴素随便是不用说了,吃住行也都很简单,唯在买书上手脚是大的。平均下来,每年所费在500元以上。到上海以后,也许是生活安定下来,做长久计了,书买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最多的1930年,总共花去2404元,平均每月约200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几个月的薪水。而到去世为止的二十多年问,鲁迅的书账加起来将近13000元,买下三处北京八道湾那样大的宅子也够了。鲁迅的收入不能算少,然要买这么多的书,总也感到吃力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