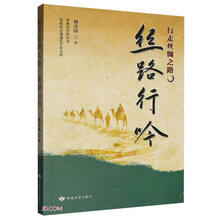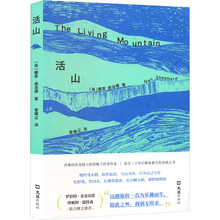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博尔赫斯谈话录》是博尔赫斯最具代表性的思想谈话集,开启博尔赫斯哲思迷宫之门的秘诀。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构小说和源于环境的小说同样真实,也许更真实。因为说到头,环境瞬息改变,而象征始终存在。假如我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街角,那个街角说不定会消失。但是,假如我写迷宫,或者镜子,或者邪恶和恐惧,那些东西是持久的——我是指它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许多人把我看成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是神秘主义者——当然,我只能感谢他们。事实上,尽管我认为现实令人困惑——而且程度越来越严重——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思想家。人们以为我专心致志于唯心主义。唯我主义或犹太教神秘哲学,因为我在小说中引用了它们。其实,我只想看看它们能派什么用处。有人认为,如果我派了它们用处,那是因为我受它们的吸引。当然,这没有错。但我只是个文人,我利用那些题材尽可能写点东西而已。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