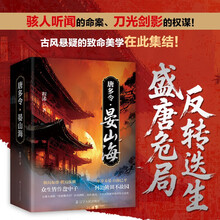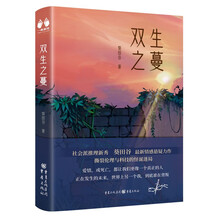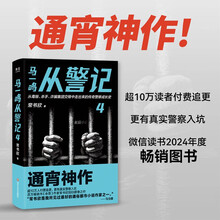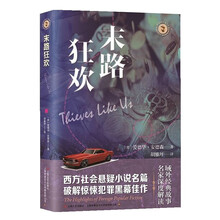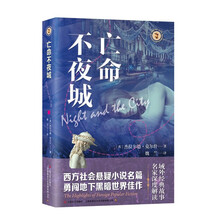1
德韦恩·迈克尔斯坐在教室的第二排,眼睛紧紧地盯着教授,希望自己能对他的课有兴趣。他的眼皮沉沉的,像是缝上了铅垂。头随着心脏跳动的节奏上下起落,而嘴巴里的味道像是有什么东西盘在舌头上死了一样。他迟到了,发现巨大的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位置:第二排的中间,正好对着讲台。
真是好极了。
德韦恩学的是电子工程,他选这门课的原因和其他工程专业的学生一样,纯粹是为了讨便宜。三十年来他们都是这么做的。“英国文学——人文主义视角”是一门不用把书翻破就可轻松通过的课程。平常教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个名叫梅休的食古不化的老家伙,他嗡嗡嗡地讲着课,就像是一个催眠师,看着四十年不变的老教案,头都不抬一下。他那低沉的声音正好让人昏昏欲睡。那老家伙甚至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考试题,德韦恩的宿舍里到处都是那些试题的复印件。可活该他倒毒,这个学期教这门课的却是一位名叫托伦斯·汉密尔顿的著名博士。大家讨好汉密尔顿的样子,就好像埃里克·克拉普顿同意在低年级舞会里演奏似的。
德韦恩闷闷不乐地挪动着,他的屁股在冰冷的塑料座位上已经麻木。他环顾左右,四周都是学生——大多是高年级的学生,要么在记笔记,要么在用微型录音机录音,惟恐错过教授讲的每一个字。教室里座无虚席,对这门课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周围没有一个工程专业的学生。
多没用的人!
德韦恩提醒自己,他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放弃这门课。不过他确实需要这个学分,而且汉密尔顿教授可能并不会为难他们。该死的,要是这么多学生认为自己恐怕过不了这门课,他们就不会在星期六上午出现在这里……会吗?
此刻,坐在前排正中间的德韦恩觉得最好努力保持清醒。
汉密尔顿在讲台边来回走动,低沉的声音一直在回响。他就像一头灰狮,长长的头发梳在脑后,身上穿着一套十分时髦的炭色西装,而不是通常那种穿旧了的粗花呢系列。他的口音很怪,不是新奥尔良本地口音,更不是美国北方口音,听上去也不完全像英国口音。他身后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助教,正在专心致志地记着笔记。
“这样,”汉密尔顿博士说,“今天我们来看看艾略特的《荒原》。这是一首包含着二十世纪所有疏离和空虚的诗歌,一首最伟大的诗作。”
是《荒原》。德韦恩现在记起来了。这是什么题目嘛!他还没想劳神去读一遍呢。为什么要读呢?这是一首诗,不是该死的小说:他可以现在就读,就在课堂上。
他拿起艾略特的诗集——是从朋友那儿借的,因为把钱浪费在那些再也不会去看第二遍的东西上毫无意义——然后翻开。扉页之后是一张作者本人的照片:一副真的是小之又小的婆婆眼镜,嘴唇撅着,像是有把两尺长的扫把在戳他的屁股。德韦恩嗤之以鼻,然后开始翻页。荒原,荒原……这就是荒原。
噢,他妈的!这不是五行打油诗。狗娘养的,它一页接着一页。
“起首的诗句如今已是众所周知,我们难以想象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二年,人们第一次在文学杂志《日晷》上读到这首诗时的那种轰动,那种震惊。这不是人们心目中的诗歌,它更像是一种反诗歌。诗人的角色已经被抹灭。这些残酷而又扰人的思想是谁的呢?当然,开篇的诗句中有暗指乔叟的著名典故,但实际内涵远不止这些。我们来看看开篇的意象:‘长在荒地上的丁香’,‘迟钝的根芽’,‘助人遗忘的雪’,我的朋友们,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诗人曾以这种方式描述春天。”
德韦恩翻到诗歌的结尾,发现这首诗有四百多行。噢,不,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