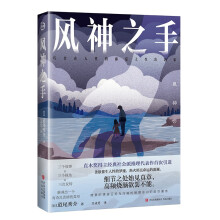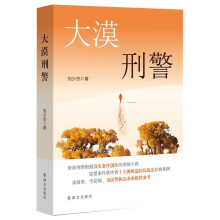开普敦来的男人
斯图亚特·M·凯明斯基
下雨了。但不是伦敦常有的溅落在雨伞和宽边帽檐上的绵绵冷雨,而是无情的倾盆暴雨,几年才有一回,在出租马车顶上奏响丛林的鼓声,让我回想起在印度经历的温带雨季。
在印度,时间过得总是很慢。而在过去两星期里,跟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在公寓度过的时间,就跟迟钝的孟买猫走路一个节奏。
我忙忙碌碌地打算为《柳叶刀》杂志写篇文章,主要是讲讲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造成的人的血液的差异,这是福尔摩斯刚刚发现的。开始他还满腔热情地踱步,抽着烟斗,打断我的写作,提醒我从犯罪学和医学两个角度来看待血液的细微差别和暗示。
但是写作进展了几天之后,福尔摩斯开始站在窗前发呆,有时候一站就几个小时,盯着被大雨冲刷的街道,不知道—个人在想些什么。
他拉过两次琴。第一次是早上五点,我被吵醒,大概是李斯特的曲子。还有一次是在下午一点,他反复地拉着一段不知名的特别哀伤的调子。
在这个不寻常的早晨,福尔摩斯坐在他的扶手椅里,拿着烟斗,看着壁炉。
“早上的《时报》里有些相当有趣的东西。”我试图挑起话题。面前起居室的桌子上还剩了些茶和吐司,是我没吃完的早餐。
福尔摩斯发出了一种搞不清是咕哝还是叹气的声音。
“利兹市的摩根·费兹莫先生,”他说,“在墓地被发现的时候朝天躺着,一枚铁轨长钉直入他的心脏。从他手抓长钉的姿势看,显然临死前曾努力想把钉子拔出来。因为夜里下过雨,除了死者本人的,警方在泥地上没有发现其他脚印。离开尸体二十步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把榔头。警方对此毫无头绪。”
福尔摩斯又咕哝了一声,然后呆呆地看着被暴雨猛击的玻璃窗。
“是啊。”我接上话头,“我说的就是这个。我以为你会感兴趣呢。”
“就那么一点点。”福尔摩斯说,“念念这篇报道剩下的部分,华生,就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费兹莫是个小毛贼。他被发现的时候是面朝上躺着的。这位死者显然并没有要防卫自己的意思。?
“对的,我看到了。”我一边往下看一边回答他。
“一个雨夜,一个小毛贼到墓地去,能干什么?”福尔摩斯吸着烟斗说,“为什么有人会拿铁轨长钉对付他?为什么没有其他脚印?为什么他没有挣扎?”
“我说不上来。”
“铁轨长钉直接就穿了进去,华生。小毛贼半夜拿着长钉和榔头去墓地,挖些小装饰品或者十字架,换点微不足道的小钱,这是很可能的。这种事在墓地常有。夜里下雨那就更好,没人会跑来撞破他的好事。”
“我没看到……”
“这种事不用看的,华生。只要用简单的逻辑,把看到的东西放在一起。费兹莫昨晚去墓地发死人财,在泥地上滑倒了,榔头也摔了出去,身子却正好压在手上拿着的长钉上。他强忍剧痛翻了个身想把钉子拔出来,已经来不及了。这里头没有秘密,华生。这是一桩意外,或者刻薄地说,是盗墓者应得的报应。”
“我们是不是该告诉利兹的警方?”
“随便你。”福尔摩斯漠不关心地回答。
“要来杯茶吗?你早饭一口都没吃。”
“我不饿。”说着,他又转头去看壁炉里噼里啪啦响的火焰,好像被万花筒般变幻的色彩催眠了。我才发现,福尔摩斯连衣服都懒得穿齐整,腿上就套了条灰裤子,衬衣上也没打领带,外边罩着几年前一个感激涕零的客户送给他的紫色丝绸便服。
上个月,有三个案子找福尔摩斯帮忙。一个是项链被盗,接着是一位俄国皮草商碰上明显属于欺诈的圈套,第三个是伦敦动物园丢失了一只豹子。福尔摩斯全部都硬生生地回绝了,让这些找上门的客户去找警察。
“如果不需要想象力,”动物园园长走了之后他说,“而且对手根本不值一提,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这种事上花时间和精力,苏格兰场那些只要稍微受过点训练的菜鸟警察就能对付了。”
他突然抬起头望着我。
“你手头有那封信吗?”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信。为了让他打起精神,很快我就从壁炉边快被烤裂的大旅行箱里把它翻了出来。烧得很旺的火堆给清晨的起居室蒙上了混乱的阴影。
这封信是几个星期前收到的,跟其他一大堆信一起,福尔摩斯也就顶多瞥了一眼。除了上面有个开普敦的邮戳,这封信没什么特别。
“再给我念一遍,华生,好吗?”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信的开头写着。
有件极为重要的事想和您面谈。我在开普敦这里要办点生意上的事,大概需要几天,不会太久。之后我就来英国,希望马上就能见到您。现在我得赶快把信送上下一班去朴茨茅 斯的船。此事牵涉金钱和爱情,对我来说甚至可能是性命攸关。恳请您给予指点。费用不成问题。
信的署名为艾尔弗雷德·唐纳伯利。
我折好信看着福尔摩斯,想不通是什么引起他的兴趣,又为什么在这个早晨想起这件事。几年来他收到太多类似的信件了。
跟往常一样,他好像看透了我心里的疑惑。
“注意一下唐纳伯利先生提到那几个‘牵涉’时候的顺序,”福尔摩斯用烟斗指着我手里的信对我说,“钱、爱情、生命。唐纳伯利先生把他自己的生命危险放在最后。古怪。说到为什么现在突然这封信感兴趣,我想问个问题。你刚才听到街上有马车停下来的声音吗?”
我承认我也听到了。
“如果查一下刚才你念过的报纸,你会发现昨天正好有一艘叫普林斯皮亚,的货船抵达朴茨茅斯港,是从开普敦开来的。如果唐纳伯利先生真如他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他很可能就是那艘船上的乘客,而且就算天气再恶劣,他也会直接找上门来。”
“也不一定是他呀。”
“那马车,从它轧过鹅卵石地面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是辆大车,不是一般的街车,是由两匹马拉的那种。没听到有其他马车的声音。时间很符合,而且,我得承认的确有点好奇,什么人会从开普敦那么远的地方特意跑来找我们。就是他,华生,如果那人果真像信里写的那么焦急,他一下船就会赶早上七点的火车来伦敦。”
有人敲门。
一丝微笑浮起,福尔摩斯满足地朝我扬了扬眉毛。
“进来,哈德森太太。”福尔摩斯喊道。
我们的女房东进来,看到福尔摩斯面前盘子里的早餐纹丝未动,不禁摇了摇头。
“一位女士求见。”她说。
“一位女士?”福尔摩斯问。
“一点没错。”哈德森太太说。
“请告诉那位女士我在等个人,她可以预定时间以后再来。”
哈德森太太收起桌上的盘子走到门口,转头又说:“那位女士让我告诉你,她知道你在等个从南非来的人。所以她才要马上见你。”
福尔摩斯弯起眉毛看看我。我耸耸肩。
“请带她进来,哈德森太太。还有,帮我们重新泡壶热茶来,好吗?”福尔摩斯说。
“你什么都没吃,福尔摩斯先生。”她说,“再给你来点新鲜饼干和果酱,怎么样?”
“茶和饼干就够了。”
小心翼翼地用一只手端着盘子,哈德森太太合上门出去了。
“看来,除了我们的唐纳伯利先生,还有别人喜欢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出门。”我说着,假装继续看我的报纸。
“看来是这样,华生。”
又有人敲门,轻轻的,只响了一下。福尔摩斯喊道“进来”。门开了,哈德森太太引进来一位优雅精致的黑衣女子。只见她皮肤白皙,乌黑的头发紧紧盘在脑后,身上一条整洁的连身长裙,扣子~直扣到脖子。她走了进来,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安静地站着,直到哈德森太太把门关上。
“福尔摩斯先生。”她温和的声音几乎不带一点重音。
“我就是。”福尔摩斯答道。
“我叫埃尔斯佩思·贝尔克奈普,埃尔斯佩思·贝尔克奈普太太,”她说,“我可以坐下吗?”
“随便坐,贝尔克奈普太太。”福尔摩斯说着指了指我旁边的椅子。
“我这次来……这真叫人尴尬,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她坐了下来,“我来是因为……”
“先问几个问题。”福尔摩斯在口袋里插着手说,“您是怎么知道唐纳伯利先生要来见我?”
“我……开普敦有个朋友,给我的信里说到的,是艾尔弗雷德办公室一个职员的妻子。”她说,“能给我杯水吗?”
我立刻起身从哈德森太太留在桌上的玻璃水瓶里倒了杯水给她。在我坐下的当口,她喝了水,看着福尔摩斯,而后者也似乎正在仔细观察她。
“福尔摩斯先生,”她说,“我曾是艾尔弗雷德·唐纳伯利的太太,直到五个月前。艾尔弗雷德是个好人。当时我父母死于约翰内斯堡的一场火灾,他就娶了我。艾尔弗雷德比我大很多。我很感激他,他对我也很慷慨。后来,差不多大半年前吧,约翰·贝尔克奈普到南非来跟我前夫一起做生意。”
“那是什么生意?”福尔摩斯问道。
“钻石生意。”她说,“艾尔弗雷德买卖钻石赚了不少钱。尽管我竭力避免,最后还是爱上了约翰·贝尔克奈普,他也爱上了我。我是个胆小鬼,福尔摩斯先生。约翰想当面跟艾尔弗雷德说这件事,但我不想有这样的场面。我劝说约翰,我们只要逃走就好了,然后我会以艾尔弗雷德的虐待和不忠为由,提出跟他离婚。”
“那么他有虐待和不忠的行为吗?”福尔摩斯问她。
她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做的事不光彩。艾尔弗雷德既没有虐待我,也没有对我不忠。他爱我,但我更多地把他当作亲爱的叔叔,而不是丈夫。”
“如此看来,”福尔摩斯说,“您如愿以偿地离了婚。”
“是的。我跟约翰一起到了伦敦。法院同意我离婚的判决一下来,第二天约翰和我就结婚了。我跟约翰私奔之前给艾尔弗雷德留了一张便条,我以为他看到后就会接受这个事实。但现在我发现……”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说,“那么,想让我帮您做什么呢?”
“劝说艾尔弗雷德别惹麻烦,离开英国,回到南非去,继续他的生活。他要是跟约翰对着干……约翰是个挺好的男人,但得看时候,要是被激怒了,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
这女人从袖子里抽出一块方巾,轻轻抹了下眼睛。
“他会使用暴力?”福尔摩斯问。
“只有在他被激怒的时候,福尔摩斯先生。艾尔弗雷德·唐纳伯利是个正派人,要是他跟约翰……”
刚说到这儿,哈德森太太敲门进来了,都没等我们说“行”。她在桌上摆了三副餐具,盘子里是饼干和果酱,另外还有一壶茶。她同情地看了看眼泪汪汪的埃尔斯佩思·贝尔克奈普,出去了。
“下一个问题。”福尔摩斯边说边拿起餐刀在饼干上涂了厚厚一层醋栗酱,“您说,您前夫很有钱?”
“相当富有。”她从我手里接过一杯茶。
“说说他。”
“艾尔弗雷德?他今年五十五岁,相貌还不错,虽然按大多数人的说法是比较亲切家常。他有点儿粗俗。我该怎么说?艾尔弗雷德没有受过教育,是自力更生的那种男人,或许有点不修边幅,但是人很好,很温和。”
“我明白了,”福尔摩斯嘴里塞着一大块涂着果酱的饼干,“他有亲戚吗?母亲?姐妹?兄弟?小孩?”
“没有。”她说。
“那如果他死了的话,谁来继承他的遗产?”
“遗产?”
“在他给我的信里,提到了钱,这也是他要见我的原因之一。”
“我想,大概是我,如果他还没有把我从遗嘱里去掉的话。”
“那您现在的丈夫呢?他富有吗?”
“约翰是个宝石商人。他的公司,伦敦彭布罗克宝石有限公司,给了他一份稳定舒适的生活。如果这是在暗示约翰跟我结婚是为了得到艾尔弗雷德的财产,我敢保证您是大错特错了,福尔摩斯先生。”
“只不过是想预测一下,唐纳伯利先生跟我见面会谈到哪方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打算付我多少钱来劝阻唐纳伯利先生进一步追究此事?”
“我以为……付钱给您?约翰和我并不富有,”她说,“但要是您能劝说艾尔弗雷德回到南非去,我愿意按您说的价钱支付报酬。我不想看到他丢脸或者受伤。”
“受伤?”福尔摩斯问。
“情感上。”她很快补充说。
“明白了。”福尔摩斯说,“我会好好考虑一下。要是接受您的请求,怎么跟您联系呢?”
埃尔斯佩思·贝尔克奈普站起来,从小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福尔摩斯。
“您丈夫的名片?”福尔摩斯问。
“背后有我家的地址。”
她对我伸出手。我握了握它,发现她在发抖。
“福尔摩斯忘了介绍我是谁。”我责备地扫了一眼我的朋友。
“您是华生医生,”她说,“我读过您记录的福尔摩斯先生的发现,相当谦恭和忠诚。”
这次轮到我微笑了。
她又转向从椅子里站起来的福尔摩斯。他握住了她的手,眼睛停留在她的婚戒上。
“漂亮的钻石和戒托。”他说。
“是啊。”她看着戒指说,“戴在手上真是浪费。对我来说,一个指环就够了,可约翰非要坚持,而他一旦想好了什么事……福尔摩斯先生,请一定要帮助我们,约翰、我,还有艾尔弗雷德。”
当她轻轻关上门离开时,外面的风雨更大了。
“迷人的女士。”我说。
“是的。”福尔摩斯说。
“爱情并非总是合情合理。”我感叹着。
“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华生。”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这事也的确够浪漫的。”我辩解道。
“走着瞧吧,华生。走着瞧。啊,她穿了斗篷,带了雨伞。明智之举。”
我听到马车关门的声音,然后听到它开动,沉重缓慢地驰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站在窗前。他不时看看手表,一直等到另一辆马车驰人贝克街的声音响起。
“我们那位被遗弃的前夫到了。”福尔摩斯转头望着我,“嗯,没错,马车停下来了。他走出来了。没带伞。大块头男人。我们在壁炉边上放把椅子吧。他肯定都湿透了。”
千真万确。当哈德森太太通报并把艾尔弗雷德·唐纳伯利带进屋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是湿的,稀疏的头发纠结在头皮上。他前妻用“亲切家常”来描述他可真是厚道。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一副愁容,唐纳伯利先生跟牛头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左手提着一只巨大的快散了架的行李箱,身上的衣服,裤子、衬衣和夹克,尽管看得出来质地很好,但都已经皱得不成样子,而且这个男人本身就很邋遢,胡子也没刮。皱巴巴的西装是深色的,有点大。
“请原谅我衣冠不整。我是直接从火车站赶来的。”他边说着,边放下手提箱,伸出手来。“唐纳伯利。艾尔弗雷德·唐纳伯利。”
福尔摩斯跟他握了握手。然后是我。握手坚定有力,神色迷惑。
“我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华生医生。请坐在靠火的地方吧。”
“谢谢你,先生。”说着,唐纳伯利走向我放在温暖的壁炉边的椅子。
“我还是直入主题吧。”他绞着手说。
“您妻子离开了您,”福尔摩斯说,“在差不多三个月前。您最近发现,她就在伦敦,所以就追着她来了。”
“你怎么知道……”
“就差那么几分钟,她就跟您碰上了。”福尔摩斯说。
“她怎么知道我……”唐纳伯利一脸困惑。
“我们暂时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福尔摩斯说,“要是可以的话,先说说您的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问题的核心?瞧你这话说的,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不,我不是来追寻埃尔斯佩思的。假如她不再需要一个老头,我能理解,尽管那很让人伤心。几个月前,在读到她留给我的便条那一刻,我就接受了事实,取下了我的婚戒。”
他举起左手,给我们看手指皮肤上一道明显的白痕,那曾是戴戒指的地方。
“您并不想找她?或者她的新丈夫?”福尔摩斯追问道。
“不想,先生。”他回答,“我不想对他怎么样。那个傲慢的家伙,把她从我身边偷走,污染了她的心灵。我想让你去找他们,阻止他们在下个月前谋杀我,别让他们得逞。”
我看着福尔摩斯,有点震惊,福尔摩斯却只不过又拿了块饼干,涂上果酱,塞进嘴里。
“为什么他们想要谋杀您,唐纳伯利先生?”我问道。
“我已经向法庭提交了修改遗嘱的申请。”他看着我说,“一个月之后,埃尔斯佩思就不再是我的遗产继承人了。”
“为什么需要一个月?”我不明白。
唐纳伯利在椅子里艰难地挪了挪身子,低头沉吟片刻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的年纪,还有偶尔不太好的健康状况,我担心自己死了以后埃尔斯佩思的日子怎么过。尽管她是法定遗产继承人,但我在康沃尔郡有些远房亲戚,他们会来抢夺遗产,起码会抢走一部分。因此,我在遗嘱中特别强调,遗产全部无条件归埃尔斯佩思所有,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撤回或者挑战我的愿望和决定。现在,我的律师通知我——这也是埃尔斯佩思非常清楚而且肯定已经告诉了她新丈夫的——修改遗嘱需要一个月时间,按谨慎的说法。你看,‘妻子’这个词并没有出现在遗嘱里,只有‘埃尔斯佩思·唐纳伯利’这个名字。”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是什么让您认为他们有谋杀的计划呢?”
“他们已经在南非对我下过两次手,”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回答我,“一次是两个星期前,我在野外。只要天气允许,灼热的太阳还能让人忍受,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平原和山区寻找宝石矿。那天特别热,有人从树林里朝我开枪,开了三枪。其中一枪就打在离我脑袋几英寸远的岩石上。我没被打死真是走运。第二次,我被推下码头,下面有三个尖桩。上帝保佑,我才掉到了尖桩之间。”
“除了贝尔克奈普和您妻子,有其他仇人吗?”
“没有。而且,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怪埃尔斯佩思,真的,是那个约翰·贝尔克奈普。这个垃圾有些狐朋狗党,而且不管他是怎么让她相信的,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知道,约翰·贝尔克奈普在经济上碰到了大麻烦。他是个浪荡子、投机分子和赌棍。我认为他要的不仅是我的妻子,还有我的财产。”
“那您是想让我保护您了?”福尔摩斯问他。
“我希望你能尽一切可能阻止贝尔克奈普杀我,或者雇人杀我。他完全是个恶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