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黄色大狗突然从黑夜中冒出,深棕色的眼睛闪着洞悉一切的光芒,彷佛在说:“你需要一只狗,就是我。”
有着猎犬血统的牠只爱追麋鹿和野牛,而对捡拾小球和树枝不屑一顾;花大钱帮牠盖了名为“丽池大饭店”的豪华狗屋,偏偏牠只爱住家里,学习从专属的狗门自由进出;牠每天都到镇上巡视一周,是街坊邻居无人不晓的“镇长”;牠是狗儿们的老大、恶狗的克星,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它是莫儿,一只来自荒野、拥有鲜明个性、充满智慧与热情的狗。作者凯拉索为莫儿开了一扇狗门,让牠自由自在探索这个世界;这扇门也让作者进入莫儿的内心世界,感受牠的忠诚、恐惧与喜悦,于是一个人与一只狗建立起充满爱与友谊、平等与互重的关系,使莫儿成为一只独立自主的狗,而不是卑微顺从的宠物。爱狗的读者必能从中找到类似的经验,莫儿的故事也促使每个人重新思考自己与狗狗的关系。
《莫儿的门》记录他们相依为命十三年的感人故事,对于人狗关系有温柔而深刻的描写。作者以充满诗意的文字描写莫儿多采多姿的生活,细腻敏锐的笔触时而幽默、时而令人悲痛心碎。读过此书你将永生难忘。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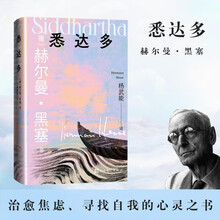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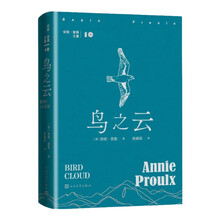

——《狗儿的秘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作者/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
《莫儿的门》是通往狗狗心灵的一扇窗,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他的忠诚、恐惧、喜悦和他真正的内心世界。只要是爱狗人士就一定要读这本书
——《倾听动物心语》(Animals in Translation)作者/葛兰汀(Temple Grandin)
时而幽默、欢喜,时而触动人心……作者对莫儿有着强烈的爱、对野外生活充满热情,这本书必将赢得众多读者的心。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这是一本充满研究精神、哲理、感性甚至令人心碎的书……莫儿过世时,作者悲伤过度难以自持,而整本书的结尾简直像艺术品般充满美感。无论你爱不爱狗,这本书的最后几句话肯定让你极度动容。
——《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 December 1, 2007)
在这本回忆录兼训练手记中,作者以充满诗意的文字描写他的狗狗莫儿,而读者若想与狗狗的关系更加深刻,本书也提供许多诀窍。
——《人物》杂志夏日阅读(People Magazine Summer Reading Round-Up)
作者让每位读者更深一层思考自己与宠物的关系。强力推荐这本书,也请多准备一些卫生纸。
——《图书馆期刊》(Library Journal)
作者讲述莫儿的故事时,同时探讨了犬科动物的行为与演化、穿插描述人狗关系的研究,并深入思考狗狗眼中的世界。莫儿是如假包换的一只狗,同时他也代表了世界上的每一只狗。这绝对是一本珍贵无比的书。
——《书目》(Booklist)杂志
这本书对于动物的聪明才智与人狗关系有着既温柔又深刻的关注。
——《柯克斯书评》(Kirkus)
在这些精深陆离的理论世界里,我和莫儿一起进入了一扇门,门内的世界陌生又熟悉,遥远又伸手可及,模糊又精确,它讲述宽容、平等、自由、爱、温暖……
——著名影星孙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