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在是一月,冬天里一个阴沉的礼拜日,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爸爸背对着桌子,脚蹬在墙上,膝上摊着一本书。妈妈坐在我的右边,她的书放在桌子上。我紧挨着她坐着,我的椅子正对着窗,离火炉很近。
桌子中间放着一壶热茶。我们每人面前都放着一杯茶和一个盘子。盘子里是汉堡和火鸡三明治。如果谁还没吃饱喝足,还有很多很多。食品柜里塞满了东西。
有时我们放下书聊起天来。这感觉真不错,就像我们是一个人,在读同一本书——而不是三个分开的人,各忙各的。
这样的日子是最完美的。
透过那个小方窗,我能望见那条通往高雷镇的狭窄的村路。村路那头,是一片雪地。雪地尽头,是我每天早上都要经过的那棵树,尽管我现在看不到。而树前面两英里远的地方,就是高雷国立小学。圣诞假期一结束,我就得回那儿去上学了。
在小路的拐角处,有一根路标立在前门左边,上面有一个箭头指向都柏林。它下面是一个稍微小一点儿的箭头,指向公墓。我们还能再在一起待两天,我们三个,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看见妈妈的书马上要读完了,就拿起一盒扑克牌,推向她的胳膊肘。很快,她就会放下书跟我玩一会儿。我看着她的脸,等着。
突然,她合上书站了起来。
“约翰,”她说,“请跟我来。”她要带我去走廊,离开爸爸。她要把我带到他的视线范围之外,就像我是一堆垃圾。“快点儿,把书放那儿。”她说。
我们站在陡峭狭窄的楼梯脚下。走上去,就是爸妈的卧室——楼上唯一的房间。她双臂抱在胸前,斜靠在楼梯扶手上。她的手冷得发白,像粉笔似的。
“我今天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她问。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又在盯着我。你在盯着我。”
“我只是看看你。”我说。
她从楼梯扶手那儿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有五英尺十英寸高。尽管我只比她矮一英寸半,她却一直使劲按着我,直到我蹲低了身子。她的身体俯在我上方,屁股向外撅着。
“你在盯着我,约翰。你不应该那样盯着人看。”
“为什么我不能看你?”
“因为你现在十一岁了。你不再是个小孩儿了。”
我被我们的猫,克利托的惨叫声分了神。它和它刚生下的小猫咪一起被锁在楼梯下的橱柜里。我想去看看它。但是妈妈更用力地按住我。
“我只是看看你。”我说。
我想说,看着什么东西一点儿也不孩子气,但是在她胳膊的重压下,我的身体摇晃了起来。我抖得太厉害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她问,“你为什么要那样盯着我?”
她弄疼了我的肩膀,她的体重真是惊人。她坐在餐桌旁或是我的床头,跟我聊天让我笑的时候,看起来要轻一些,小巧一些,也更漂亮一些。现在我对她非常生气,她怎么那么高,那么大,那么重,她怎么把我生得这么大,远远大过我的年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我说。
“也许你应该改掉这个习惯。”
“为什么?”
“因为那让人紧张。你那么盯着看,谁都没法放松。”
“对不起。”我说。
现在她站起来了,放开了我。我倾身过去,吻在她嘴边上。
“没事了。”她说。
我又亲了她一口,但是当我抱住她的脖子,想把她拉近,这样就可以抱紧她了,她却挣开了。“现在别,”她说,“这儿太冷了。”
她转过身去,我跟在她后面,走回厨房。
爸爸那黑色的卷发凌乱不堪,刘海全挡在了眼前。“关门。”他说,视线没离开书。
“已经关上了。”我说。
“好,”他说,“一直让它关着。”
他看着书笑了,那是本《颅相学和罪犯颅骨》。
爸爸已经三年没工作了,这期间我们一直住在他妈妈的农舍里。搬来和奶奶一起住之前,他在威克斯福德当电工。但是他恨他的工作,每天回家他都这么说。现在,他不去上班了,而是在家读书。他说他要准备圣三一学院的入学考试,要通过它应该不会有太多麻烦,因为去年他参加过门萨测试,分数很高。
“看窗外,”我对妈妈说,“雪在横着下。”
“是啊,”她说,“像不像在筛面?”
“面粉不会横着穿过筛子。”我说。
她把舌头伸出来舔了舔嘴角,然后就停在了那儿。我探身过去摸了一下。
“你的舌头很凉。”我说。
爸爸看着我们,妈妈的嘴唇夹得紧紧的。
“我像条蜥蜴。”她说。
她对我微笑,我也对她微笑。
“奇怪的一对儿。”爸爸说。
克利托现在很安静。很可能听到我们在聊天,知道我们离它很近,它就高兴起来了。
我又开始读《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是我最喜欢的书。除了1959年版,我拥有这本书的其他所有版本,这是我每年的圣诞礼物之一。
这本1972年的新版还剩下几页没读。“人类世界”这部分,我差不多快读完第四遍了。 《士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充满了奇迹,比如那个中国牧师,他保持着最长指甲的世界纪录。他的指甲养了二十七年,足足有二十二英寸长。照片上,那些指甲乌黑卷曲,就像公羊角。
其中最棒的是那些逃脱艺术家,还有那些奇人异士,比如布朗汀,他走在钢索上穿越了尼亚加拉大瀑布,还有约翰?赫林格,他用手走路走了五十多天,整整八百七十一英里。
总有一天我也会被写进《士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和所有那些不想被忘记,不想被忽略的人一起。我会打破一项非常重要的世界纪录,或是做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我看不到活着的意义,除非有某件事我能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好,或者我能做某件其他任何人都做不了的事。
我把世界上最矮的女人的照片折了起来,这样她就正对着世界上最高的男人了。他的名字是罗伯特?珀欣?瓦德罗。他有八英尺十一点一英寸高。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六英尺七英寸高了。
我曾经想,他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很早就变了声。我曾经想,我是不是也会变成一个巨人。现在我还是会担心这些事,不过没有当初那么厉害了。因为我已经决定,我不会作为一个畸形出现在《士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里。我要有一个比那好得多的理由。
世界上最矮的女人是波林?莫斯特斯,她才一英尺十一点二英寸高。当我把她的照片和世界上最高的男人放在一起时,她看起来就像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的什么东西,一点儿都不像人:一个人怎么可能站在另一个人的身边,还不到他的膝盖?
“看,”我对妈妈说,“这个侏儒像个砖寺。”
我就知道她要说什么。
“装饰。”她说。
“别折你的书。”爸爸说。
“好的。”我说。
“你都没怎么碰三明治。”他说。
“我不想碰。”我说。
妈妈拍拍我的手。“你留着一半三明治没吃,是不是就为了说这话?”
“不是。”
“那就把它吃完。”
但是面包已经不太新鲜了。已经六点了,该喝茶了。妈妈站起来看向窗外。雪停了。她在运动衫上揩揩手,把一壶水放在火炉上。她打开冰箱,取出一个盒子。
“你要这个吗?”她问爸爸。
他揉着下巴,没有回答。他昨天把胡子剃了,剃完之后,脸上就露出了一个酒窝;在下巴上有一道暗色的竖沟。一整天他都在揉它,好像希望能把它揉平。
“迈克尔,你喝茶要不要这个?”
他看着那个盒子。“不要,”他说,“我更想要腌鱼。”
“我们没有,”妈妈说,“我们没有腌鱼。”
妈妈讨厌做饭。
“那我就吃袋装鱼。”他说。
“那好。”她说。
他们彼此笑了一下,和他们给我的笑不一样。爸爸说的袋装鱼是一种要用沸水煮的食物:一块方方的鱼肉,装在一个盛满白色调味汁的透明塑料袋里。
“能让我拿一下它吗?”我问。
“如果你真想拿的话。”妈妈说。
我从她手里接过袋子,双手揉着塑料。塑料很软,就像湿毛毡。
“好像我在巴特林斯赢的金鱼。”我说。
“到我这儿来。”爸爸说。他抱住我,他的胳膊重重地压在我的脖子上,他搂得太紧了。
“别搂我的脖子,”我说,“疼。”
“把鱼袋子给我。”他说。
我把袋装鱼递给他,他轻轻地抚弄着。“恐怕我得有不同意见了,”他说,“这更像一袋鼻涕,而不是金鱼。”
爸爸笑了起来,我也笑了,尽管我不喜欢他把我的晚饭比作鼻涕。
妈妈没收了鱼,把它放进一壶水里。我面对着爸爸。
“老爸,给我讲个故事行吗?”
“什么样的故事?”
“什么样的都行。”
开始讲故事之前,爸爸清了清嗓子,然后在座位上坐直了身子。“好,那就讲个坦塔罗斯的故事。他犯了错,被罚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冬天,那水寒冷刺骨;夏天,又热得烫人。当坦塔罗斯口渴的时候,他的嘴唇特别干,于是就弯腰去喝水,但是水却突然蒸发了。当他肚子饿的时候,就伸手去够头上那结满美昧水果的树枝,但树枝却突然把水果举高了。食物和水他都够不着。坦塔罗斯受这种苦受了……”
“好几天,”妈妈说,“这都是因为他喝茶前不洗手,才会受到这种惩罚。后来他坐到了一桌有烤鸡和巧克力冰淇淋的盛宴前,从此再也没挨过饿。”
爸爸笑了,“去洗手吧。”
洗手的时候,我看见坦塔罗斯一边弯腰够水,一边舔着嘴唇。在回厨房的路上,我走到起居室那个大书架旁:那是爸爸放资料和课本用的。我在百科全书里翻着,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那几页。是西西弗斯那条,他的名字旁边有个红色的感叹号,那是我去年画上去的。我回到厨房。
“坦塔罗斯和西西弗斯很像,”我说,“可以说,他们两个受的是同样的苦。”
爸爸笑了起来,“是不是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想起来的?”
“我没坐在马桶上。我就是洗了洗手,然后突然想起来了。”
我仔细地打量他的脸。他不是在笑话我,所以我也笑了起来。
“是的,”我说,“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西弗斯把那块大石头推上山,然后那石头从他身边径直地滚下去,又落回到山脚下。我可以看到西西弗斯站在那里,看着那块石头滚下去,他是那么悲伤,但是一言不发。然后他又把那块石头推上山,然后石头又滚回它原地,一次又一次。我想他的感觉肯定就跟坦塔罗斯一样。”
“竭尽全力把那个棕色的大东西弄到你想让它去的地方。”爸爸一边说,一边大笑着,笑得眼里全是泪。
现在轮到妈妈笑了。“老天,”她说,“谁去给这个可除的家伙拿杯水?”
我跳了起来,去给爸爸接了杯水。我坐回去的时候,妈妈吻了我的鼻子一下作为感谢。“有你在身边真好,”她说,“我想我们会留着你。”
“很好。”我说。
爸爸把水一饮而尽,这时我看见他夹克的扣子系错了。他是故意的,这通常是心情好的标志。我探身过去,伸手去够最上边的扣子。
“我给你系扣子可以吗?”我问。
“不,不!”他大笑,“你会毁了我流里流气的形象。”
看来他蛮有兴致让我帮他系好扣子,于是我绕过桌子,伸手去抓第二颗扣子。他又喊又笑。
“离我远点儿,鱼脸!离我远点儿!”
“还有四颗了!”我冲他喊回去。
我试图再解开一颗扣子,他突然站了起来,走向窗边。他站在那儿,向外看去,他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游戏结束了。
“主啊,我想她提前回来了。”
“是吗?”我问。
他在说奶奶,也就是他的妈妈,她周二会从李奥柏的赛马会回来。我只能再和他们单独待两天。
“不,”他说,“一个虚假的警报。”
我们坐了下来,他又开始读书。
我面对着梳妆台,所以能看见1960年他们结婚那天照的黑白照片。爸爸那会儿二十七岁,甚至比现在还要帅,因为他当时的头发更长些。妈妈那会儿二十六岁,她现在还一样漂亮。
几乎整个威克斯福德教区的人都知道我父母的爱情故事。他们各自退掉了原来的婚约,选择了和对方在一起。我听说,当他们走在街上时,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看他们:他们简直就像电影明星。
照片里,他们看上去十分开心。爸爸站在妈妈身后。他比她高了四英寸,所以让她看上去小巧了点儿。我喜欢他们一起切蛋糕的样子,妈妈的手放在爸爸的手上,共同握着一把白柄的长刀。
我一点儿都不帅,又瘦又高,我的鼻子对于脸来说太大了。爸妈看我的时候肯定很难受,一定在琢磨我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变得像他们一样漂亮。
我回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开始读三百九十八页上关于被活埋在一个“标准”棺材里的世界纪录。这项纪录是由一个叫蒂姆?海斯的爱尔兰男子保持的。他被活埋了二百四十小时十八分钟五十秒。1970年9月2日,他出来呼吸了口新鲜空气。我很惊讶,我竟然从来没听说过他。也许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他。
快七点了,我开始觉得无聊。我把脚放在妈妈的脚上,她把脚抽出去,又放在我的脚上。我们来来回回,爸爸朝我们看,摇了摇头。我没让他发现我已经注意到了,但是这个缓慢的摇头立刻让妈妈停了下来。她站起身,看了看表。
“你最好克服一下,把活儿干了。”她对爸爸说。她说的是克利托的小猫咪。在奶奶回来前,得把它们杀掉。
“等一会儿。”他说。
“请在某人给它们起名之前把事儿干了,”妈妈说,“约翰,你和我待在这儿。”
“我不在乎,”我说,“这次我要去帮忙。”
“我也不在乎,”她说。她看着爸爸,“要赶在你妈回来之前摆脱这些小东西,不然就永无宁日了。”
爸爸给我们的猫起了个和苏格拉底最好的朋友一样的名字——克利托,苏格拉底临终之时,他哭得最厉害。我喜欢克利托黑白相间的脸和它长长的白色小腿。
妈妈对着爸爸摇了摇头,他站了起来。“那就来吧,”他说,“让我们 看看这个小男孩是什么做的。”
我跟着他走到楼梯下的橱柜旁。他蹲到煤烟的黑暗之中,蹲在吸尘器和煤铲之间。他让我把灯打开,然后就拉着那六只小猫的尾巴把它们从克利托的奶头上拽了下来。他的夹克塞在裤子里,腰上就形成了一个口袋,他把小猫咪放了进去。
“没事的,”我对克利托说,“我们带它们去散散步。”
“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爸爸问。
“是的。”我说。
“那就去煤桶里取条麻袋,把它带到浴室去。我会在那儿等你。”
听起来就像我们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但这农舍是个小地方,没有人会在里面迷路的:你走进前门,就站在了走廊里,如果你向右转,就会走进厨房,从厨房你可以走回走廊,或者走到起居室。起居室有两个门,你可以出去,又走到走廊,面前是一扇门,里面是浴室。再往前走几步,你就可以看到我卧室的门。然后,在农舍的后部,你会发现奶奶的卧室。走廊尽头就是后门,它通往一个小花园。唯一算得上冒险的就是爬上狭窄的木楼梯,去爸妈的卧室看看。
我把麻袋放在爸爸的脚边。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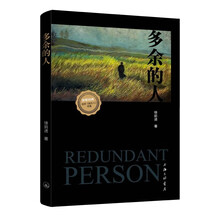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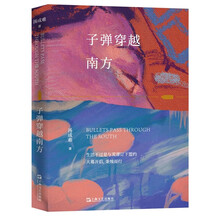




——诺贝尔奖得主库切
一个少年的迷惘与慌张……约翰的喃喃自语充满着力量……故事微妙的结局令人满意,它足以使约翰跻身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并成为本年度最值得记忆的人物之一。
——《出版家周刊》
一部快节奏的心理剧……新鲜宜人而又充满矛盾,让我们想起丢失纯真的疼痛,和追逐真理的代价。
——《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