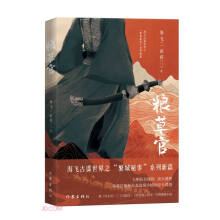巴斯克斯·蒙塔尔万(Manuel Vazquez Montalban,1939-2003),西班牙当代著名小说家、诗人、专栏作家、社会评论家、美食家。<br><br> 蒙塔尔万出生于工人家庭,早年在巴塞罗那大学主修哲学与文学。他曾参加反佛朗哥独裁政权的学生运动,并担任过西班牙共产党地方党派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主要领导人。<br><br> 自1972年出版小说《我杀了肯尼迪》开始,他创作了二十部以巴塞罗那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塑造了卡瓦略这个西班牙文学中最著名的侦探形象。他因此而获得美国雷蒙德·钱德勒奖。<br><br> 2003年,蒙塔尔万在从澳大利亚返回西班牙途中,在曼谷国际机场转机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