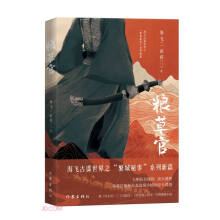关于叙述的欲望
在我写作的时候,强烈的怀疑折磨着我:我到底可不可以叙述这一切?我自己是否没有更好地保守这一切,就像那些迄今为止知道这一切的人一样。但是,沉默不是最残忍的谎言吗?难道错误无助于理解真相?让真正的基督教徒一生都不知道、始终逃到信仰的见证中去的那种知识本身让我不能决断。我一直在斟酌赞成还是反对,直到叙述这个故事的欲望剧增——正如我在一些重要的情况下体验到的欲望一样。
我喜欢修道院。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促使我到这些与世隔绝的地方。有人曾经察觉到,修道院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喜欢修道院,因为在那里,时间似乎停滞。我享受这些有若干侧翼的大楼都弥漫的那种病态气味。这种混合气味来自永远散发霉味的大开本书、被擦得潮湿的过道和挥发的香烟。但是我尤其喜欢修道院里的花园。在多数情况下,公众都看不见这些花园。为什么我知道?不过,正是这些花园展现了乐园的景色。
在先讲述这一点的时候,我要解释为什么我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闯入本笃会修道院乐园。阳光明媚只有在南方的天空才可能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导游礼拜堂、礼拜堂地下室和图书馆以后,我成功地脱离团队。此时,我发现了一条穿过小侧门的道路。据估计,小侧门的后面可能就是按照圣人本笃的规划修建的修道院花园。
这个小花园非常小,比一个这么大的修道院所期待的小得多。加强这种印象的是,落日斜穿这个正方形乐园,把乐园分成明亮的一半和背阴的一半。修道院里凉气袭人,令人心神不安。之后,太阳的温暖显得很令人舒服。夏末正是福禄考和大丽花盛开的季节,花朵都沉重而下垂:而蝴蝶花、唐菖蒲和羽扇豆则竖直向上生长。在狭长的莱畦里,各种各样的芳香菜密密麻麻地疯狂生长,分开它们的是普通的木板。不,这个修道院花园与其他本笃会修道院里类似公园的设施没有共同之处,围绕在四周的是密集的防御性大楼侧翼,倚靠着一个环绕的十字形回廊,可以与世俗建筑如凡尔赛宫和丽泉宫媲美。这个修道院花园曾是生荒地,后来堆积成为修道院南坡的梯地,支撑它的是一道凝灰岩高墙,像花园从这个地方生长出来一样。南边视野开阔。在天空明朗的日子里,人们可以看清地平线上的阿尔卑斯山脉。在香莱生长的另一侧,水汩汩地从铁管流入石槽。石槽旁边是一间枯朽的园中小屋,更确切地说,那是用木板隔开的房间。已经有好几个建筑工程师都很笨拙地试着去维修这个房间。防雨的是已经破烂了的屋面油毡覆盖物。横放的破旧窗扇是唯一的进光洞口。整个一切都在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传播喜悦。或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建筑物用某种方式让我们想起我们孩提时代在假期一起搭建的木板小房子。
突然从背阴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孩子,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保护性地用手挡住眼睛,以便在逆光中认清形势。我看到的景象让我吓呆了一会儿:在那里,一个修土蓄着先知的雪白胡须式样,端坐在轮椅上。他穿着一件带点灰色的衣服。那衣服与本笃会修士雅致的黑色明显不同。在他用折磨人的目光打量我的时候,他把头转来转去,目光没有离开我,像一个木偶。
尽管我很明白他的问题,可我为了赢得时间,还是反问道:“您是什么意思?”
“孩子,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那个奇怪的修士用同样的头部动作重复了他的问题。我相信在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一种空洞的神色。
我的回答仍然是干巴巴的。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次奋怪的遭遇和他那同样奇怪的问题。“我没有寻找您。”我说,“我参观这个修道院,只是想看一下这个花园。对不起,打扰您了。”当那个老人突然让到那时为止放在轮椅扶手上一动不动的手臂形成一个角,驱动轮子,以便他像从弹射椅子上弹出来一样,加快速度冲向我的时候,我;隹备用点头同意来告别。那个老人似乎有熊的力量。他停住了,和他逼近我的时候一样快。当他离我十分近的时候,我当时不管阳光的照射,看清了成绺的头发和胡须下面那一张狭长的惨白的脸。他比第一眼看起来的时候年轻得多。这种遭遇开始让我感到不安。“你知道先知耶利米吗?”那个修士直截了当地问。我犹豫了片刻。我考虑干脆跑开。但是他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和那个男子散发出来的奇怪的威严让我留了下来。
“知道。”我说,“我知道先知耶利米与以赛亚,巴禄、以西结、但以理、阿摩司、撤迦利和玛拉基。”——就像自从上修道院寄宿学校以来这些人就留在我的记忆中一样。
答复让那个修士目瞪口呆。对,答复似乎让他很高兴,因为他脸上的呆板一下子消失了。而且他动作起来也不再像木偶。
“到那时,”耶利米说,“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事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殓,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人民在我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拣死不拣生。”
我疑惑地看着那个修士。那个修士看出我迷惘的目光,就说:“《耶利米书》是这么说。”
我点头表示同意。
那个修士抬起头。他的白胡须几乎是横着长的。他用手背轻轻地掠一掠华发的下边。“我是耶利米。”此时他说。他声音的语调听起来有一种自负,一种完全不是修士的德性。“大家都叫我耶利米修土。但是这说来话长。”
“您是本笃会的修土?”
他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有人把我藏在这个修道院里,因为在这里我造成的损失可能最小。按照圣人本笃的教规,我就这样生活,对世俗生活需求无动于衷,作为格格不入的人有失尊严。假如我可以,我会逃走的。”
“您来这个修道院还没有很久吧?”
“数个星期。数个月。也许已经数年。这有什么关系?!”
修土耶利米的抱怨开始引起我的兴趣。我适度谨慎地打探他以前的生活。
这时,那个神秘的修士沉默了。他让下巴垂到胸部,看着已经瘸了的双腿。因此,我觉得我的问题太过分了。但是,还在我准备表达歉意的时候,耶利米开口讲话了。
“孩子,你知道米开朗基罗……吗?”
他结结巴巴地讲,没有抬头看我。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说出每句话的时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我觉得:他的话没有条理,话语之间没有关联。我记不起任何细节。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他一直语无伦次,一直在更正和重复一些句子。但是我记得,梵蒂冈城墙后面正在暗中进行一些事情。基督教信徒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而且教会是个纯洁的婊子——这让我吓了一跳。此外他使用术语,陶醉于论争神学、道德神学和教义学。耶利米修士可能神志不清,我的这种怀疑消失了,比怀疑来的时候更快。他用名字和年份讲解宗教会议,区分地方会议、省级会议和全体大会,列举主教派教会的优点和缺点,直到他突然一下子停下来,问:“或许你也认为我疯了?”
是的,他说“也”。这让我很吃惊。显然,有人把耶利米修士当作精神病人隔离在这个修道院里,他像个讨厌的异教徒一样。我也不再知道我如何回答那个修士。我只记得我对这个男子越来越有兴趣。因此,我回到了我的问题,请求他跟我讲讲他是如何到这个修道院的。但是,耶利米把他的脸转向太阳,闭着眼睛不说话。在我这样打量他的时候,我留意到他的胡须如何开始颤动。这种细微的颤抖越来越剧烈。那个修士的整个上身突然开始抽搐。他的嘴唇在颤抖,像高烧在折磨他一样。在这个男子闭上眼睛以前,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件呢?
修道院礼拜堂塔楼的钟声敲Ⅱ向了,召唤大家共同祈祷。当耶利米修士从梦中惊醒的时候,直起身子。“不要跟任何人讲关于我们碰面的事情。”他急急忙忙地说,“你最好藏在园中小屋中。在晚祷的时候,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个修道院。明天同一时间再来!我会在这里等你!”
我遵照那个修士的嘱咐,藏到了小木屋里面。之后,脚步声马上逼近了。我窥视半明半暗的窗户外面,看见一个本笃会修土把轮椅上的耶利米推到礼拜堂。他们俩都没有说话。似乎没有人注意别人。这个人似乎在按照一个不容改动的程序办事,而另一个人无动于衷地容忍他。
不久以后,我听见礼拜堂传来格列高利圣歌,我走出外面去。然而在园中小屋的影子中,我停住了脚步,以便不会有人从周围的修道院大楼的某个窗户那里发现我,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想再见到耶利米修士。在支撑墙旁边,一条陡峭的石梯向下延伸。一扇锁住入口的铁门是容易越过的。
我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修道院和天堂花园。第二天我走同一条道路进去。一个教友把轮椅上的耶利米推到花园里,像前一天那样一言不发。之前我肯定没有等多久。
“自从我到这里以来,没有人对我过去的生活感兴趣。”那个修士开门见山地开始说,“相反,他们竭力忘记我过去的生活,让我与世隔绝。他们让我相信我可能已经失去理智,似乎我是一个颓废的修土,一个属于伊斯兰教阿萨辛派别的刺客。关于我的全部真相、可能没有在这个修道院里传开。尽管我恳求他们上千次,可还是没有相信我。伽利略的感觉肯定与我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同。”
我申明我相信他的话。我感觉他有一种让别人相信的需求。
“但是我的讲述不会让你更加幸福。”耶利米修士提出异议。我申明我会懂得去忍受他的讲述。这时,那个孤独的修士才开始讲述。他讲起来心平气和,甚至有时采用陌生化的手法。第一天我对他自己为什么没有在故事中出现表示惊讶。第二天我渐渐明白,他采用第三人称讲述自己,仿佛是一个中立的观察者——对,他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的人之一肯定就是他自己:耶利米修士。
我们在那个修道院天堂花园里接连五天见面。我们躲藏在枝繁叶茂的玫瑰花棚后面,有时也藏在枯朽的小屋里面。耶利米讲述,列举名字和事实。尽管有时觉得他的故事很离奇,可我一点也不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只是在耶利米讲述的时候,他很少看着我。在多数情况下,他的目光都指向远方想象中的一个点,似乎他在看一块黑板。哪怕是一次我也不敢打断他的讲述,我不敢提问,因为我担心他会失去线索,因为我被他的讲述迷住了。我也避免做笔记。做笔记也许会干扰那个修士的流利讲述。因此我是凭记忆记录下面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下面的故事接近耶利米修土的原话。
罗马教廷决定按照最新的科学知识修复西斯廷礼拜堂的那天是讨厌的。佛罗伦萨人是讨厌的,一切艺术都是讨厌的,胆大妄为是讨厌的。唱反调者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用——所有岩石中最令人讨厌的——石灰粉,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湿壁画中夹杂着淫荡的色彩。
枢机主教耶里内克望着高高的穹顶。帆布帐篷罩住了穹顶。从穹顶那里垂下一个支架。他正好看见上帝手指旁边的亚当。他似乎敬畏神的强大权力,枢机主教的脸上掠过一种明显的抽搐,没有规律地间歇性出现多次。因为在画中,周围都是红色的法衣,在飞的神并不仁慈。上帝显现了,充满力量,很美丽,像斗土一样浑身都是肌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肌肉)这个词在这里变成了肉感。
自从懂艺术的教皇尤利乌遭遇厄运的时代以来,没有教皇从米开朗基罗放荡画中找到快乐。米开朗基罗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个公开的秘密:他对基督教信仰表示怀疑。当时,他那些画的思想来源于《旧约》和希腊古代作品的奇怪糅合,也许还来源于理想化的罗马气派,这完全被当作有罪。据说,当这个艺术家第一次揭开无情上帝的湿壁画的时候,教皇尤利乌跪到地上祈祷。上帝让好人和坏人都因为他审判的权力而战抖。不过教皇还没有从他的谦恭中回过神来,他就陷入了与米开朗基罗关于绘画的陌生、神秘和赤裸的激烈争论。讳莫如深的象征、无数的影射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暗示把罗马教廷搞得不知所措。当这一切叠加在一起的时候,罗马教廷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指责赤裸裸的人,更有甚者,要求清除这一切。特别是教皇的典仪官切塞纳相信从地狱判官麦诺斯可以看出自己的影子。只有这个罗马最重要艺术家愤怒抗议,《末日审判》才没有被拆除。
渗透水、多次涂抹上去的颜色和蜡烛灰将要毁坏米开朗基罗的放荡的飞神。哦,霉菌真的会侵蚀画中的先知,香烟会损坏画中的女巫们。因为首席修复专家菲德里兹还没有开始在高高的支架上工作,还没有和助手们一起清除由炭灰、黏液和在油中才溶解的颜料构成的深色层,此时这个佛罗伦萨人的遗嘱不可抑止,米开朗基罗似乎复活,像复仇之神一样具有威胁性。
当时,先知约珥手中拿着一卷字迹模糊的羊皮纸文稿。在左右手之间,文稿从前面向后面翻转。手写的字符既不在文稿的正面,也不在背面。在成功清除深色层以后,而今在书卷上清晰可见字母A。希腊文第一个字母A和最后一个字母O是基督教教会最初的象征。但是修复专家徒劳地擦拭,直到用湿灰泥涂画的文稿变成刺眼的白色。涂画的湿灰泥遮住的不是字母O。在放在阅读架上的埃利色雷的女巫们与先知约珥相邻的书中出现了另一个神秘的简约记号:I—F—A。这个出人意外的现象不为公众所知地引起了激烈讨论。以帕瓦内托教授为首的梵蒂冈建筑与博物馆的馆员和艺术史学家鉴定这个发现。米开朗基罗专家帕伦蒂从佛罗伦萨赶来。在秘密磋商字母I—F—A的含义以后,罗马教廷枢机国务秘书卡斯科讷把这个发现说成秘密事情。帕伦蒂也是第一次谈及在修复过程中可能发现其它字符的可能性,而破译这些字符或许不是罗马教廷和教会所希望的。归根到底,米开朗基罗饱受他的委托人教皇们之苦,不只一次暗示他会用他的方式进行报复。
枢机国务秘书探询可不可以预料到这个佛罗伦萨画家的异教思想。
艺术教授有保留地肯定了这个问题。
之后,枢机国务秘书卡斯科讷让神圣的教义部部长、枢机主教耶里内克去处理这件事情。然而,耶里内克对这件事没有多大兴趣,并且建议:帕瓦内托教授领导的梵蒂冈建筑与博物馆总经理团队可能关心这个情况——假如确实有人谈及这个情况。这个神圣的政府官员不愿介入。
当第二年修复先知以西结的画像的时候,罗马教廷的兴趣首先指向耶路撒冷毁灭的宣告者左手中握的书卷。菲德里兹报告,看样子好像湿壁画在这个地方被熏得特别黑,好像是用蜡烛火焰人为地加深这个地方的颜色的。最后在修复者的海绵下面显现另外两个字母L和U。帕瓦内托教授表达了他的猜测:次序排在以西结后面的波斯女巫也藏有一个秘密的字母。驼子老人显然近视,把一卷红色的书直接拿到眼前。从支架那里近看,在菲德里兹进行清扫以前已经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个字母。看起来这个发现让枢机国务秘书比所有别的人都更加不安。他让人尝试去清扫那个女巫的书。因此,猜测变成肯定。字母组合多了一个B。
那么,肯定可以由此推出,次序最后的一个画像先知耶利米同样也会现出一个简约记号。事实上,在他一侧的书卷显现A。耶利米不像别的先知受到内心挣扎的痛苦,坦率说出这个民族永远都不会改变信仰。米开朗基罗为耶利米画出一副他自己绝望的面孔。耶利米仍然一言不发,听天由命和不知所措——他似乎知道字母序列A—I—F—A—L—U—B—A的神秘含义。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