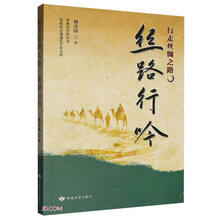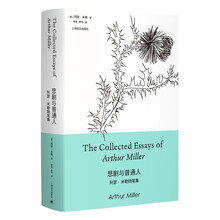苍茫之悟
很久以来,面对苍凉的荒漠,迷茫的雪原,无法逾越的高山,浩渺无垠的大海,心胸就被一种异样的激情壅塞,骨髓凝固得像钢灰色的轨道,敲之当当作响,血液打着漩涡呼啸而过,在耳畔留下强烈的回音,牙齿因为发自内心的轻微寒意,难以抑制地颤抖,眼睛因为遥远的地方,不知不觉中渗透泪水……
当我十六岁第一次踏上藏北高原雪域,这种在大城市从感受的体验,从天而降,它像兀鹰无与伦比的巨翅,攫取了我的意志,我被它君临一切的覆盖所震惊。
它同我以前在文明社会中所有的感受相隔膜,使我难以命名它的实质,更无法同别人交流我的感动。
心灵的盲区,语言的黑洞。
我在战栗中体验它博大深长的余韵时,突然感悟到——这就是苍茫。
宇宙苍茫,时间苍茫,风雨苍茫,命运苍茫,历史苍茫,未来苍茫,天地苍茫,生命苍茫。
人类从苍茫的远古水域走来,向苍茫的彼岸划到小舟,与生俱来的孤独之感,永远尾随鲜活的生命,寰宇中孤掌难鸣,但不屈的精灵还是高昂起手臂,彷佛没有旗帜的旗杆,指向苍穹……
痛苦的人生,没有权利悲哀,
苍茫的人生,没有权利渺小。
比树更长久的
人们对于生命比自己更长久的物件,通常报以恭敬和仰慕。对于活的比自己短暂的东西,则多轻视和俯视。前者比如星空,比如河海,比如久远的庙宇和沙埋的古物。后者比如朝露,比如秋霜,比如瞬息即逝的流萤和轻风。甚至是对于动物和植物,也是比较尊崇那些寿命高渺的巨松和老龟,而轻慢浮游的孑孓和不知寒冬的秋虫。在这种厚此薄彼的好恶中,折射着人间对于时间的敬畏和对死亡的慑服。
妈妈说过,人是活不过一棵树的。所以我从小就决定种几棵树,当我死了以后,这些树还活着,替我晒太阳和给人阴凉,包括也养活几条虫子,让鸟在累的时候填饱肚子,然后歇脚和唱歌。我当少先队员的时候,种过白蜡和柳树。后来植树节的时候,又种过杨树和松树。当我在乡下有了几间小屋,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园子之后,我种了玫瑰和玉兰,种了法桐和迎春。有一天,我在路上走,看到一节干枯的树桩,所有的枝都被锯掉了,树根仅剩一些凌乱的须,仿佛一只倒竖的鸡毛掸子。我问老乡,这是什么?老乡说,柴禾。我说我知道它现在是柴禾,想知道它以前是什么?老乡说,苹果树。我说,它能结苹果吗?老乡说,结过。我不禁忿然道,为什么要把开花结果的树伐掉?老乡说,修路。
公路横穿果园,苹果树只好让路。人们把细的枝条锯下填了灶坑,剩下这拖泥带土的根,连生火的价值都打了折扣,弃在一边。
我说,我要是把这树根拿回去栽起来,它会活吗?老乡说,不知道。树的心事,谁知道呢?我惊,说树也会想心事吗?老乡很肯定地说,会。如果它想活,它就会活。
我把鸡毛掸子种在了园子里。挖了一个很大的坑,浇了很多的水。先生说,根须已经折断了大部,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大的坑,又不是要埋一个人。水也太多了,好像不是种树,是蓄洪。我说,坑就是它的家,水就是它的粮食。我希望它有一份好心情。
种下苹果树之后的两个月,我一直四处忙,没时间到乡下去。当我再一次推开园子的小门,看到苹果树的时候,惊艳绝倒。苹果树抽出几十支长长短短的枝条,绿叶盈盈,在微风中如同千手观音一般舞着,曼妙多姿。
我绕着苹果树转了又转,骇然于生命的强韧。甚至不敢去抚摸它紫青色的树干,惟恐惊扰了这欣欣向荣的轮回。此刻的苹果树在我眼中,非但有了心情,简直就有了灵性。
当我看到云南个旧市老阴山上的文学林的时候,知道自己又碰上了一群有灵性的树。1983年的春天,丁玲、杨沫、白桦、茹志娟、王安忆等二十多位作家,在这里种下了树。二十一年过去了,我看到一棵高高的杉树,上面挂着一个铭牌,写着“李乔”。李乔是位彝族作家,已然仙逝。我没缘分见到他本人,但我看到了他栽下的树。以后当我想起他的时候,记不得他的音容笑貌,但会闪现出这棵高大的杉。李乔已经把生命的一部分嫁接到杉的枝叶里,这棵杉树从此有了自己的名姓。
也许是考虑到每人一棵树,不一定能保证成活,也不一定能保证多少年后依然健在,这次聚会,栽树的仪式改为大家同栽一棵树。这是一棵很大的树,枝叶繁茂。我也挤在人群中扬了几锹土,然后悄悄问旁人,这是一棵什么树?
是棕树的一种,国家二类保护树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棵树能活多少年呢?我又追问。
这个……不大清楚。想来,一百年总是有的吧。工作人员沉吟着。
我看着那棵新栽下的棕树,心想不管它的寿命多么长久,总有凋亡的那一天。也许是被雷火劈中,也许是山洪冲毁,也许是冰霜压垮,也许是盗木者砍伐……总之,一棵树也像一个人一样,有无数种死法,总之是不会永远长青的。
在栽树的时候,去谋划一棵树的死亡,这近乎是刻毒了。我不想诅咒一棵树。鉴于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人们寄希望于那些比个体生命更悠远的事物。但一棵树也是会死的,即使像我捡来的苹果树那样顽强且有好心情的树,也是会死的。既然树木无望,我们只有寄托于精神的不灭。
一个人是活不过一棵树的,然而再古老的树也有尽头。在所有的树的上面,飞翔着我们不灭的精神,而文学是精神之林的一片红叶。
最大的缘分
这几年,“缘”字泛滥,见面就是缘,好像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是个笨人,坐在飞机上,不相识的邻座要我在他的本上写句话,憋了半天,写了句“——机缘”,还暗中得意好久,以为急中生智。
在翠绿的伊犁河谷,一位哈萨克少女,高擎着马奶子酒说,尊贵的客人,世上最高最长远的缘分是什么呢?是吃啊!一生下来,婴儿就要吃。到不能吃的时候,缘分也就尽了。人们因吃而聚,因吃而离……
那一天,所有的味道,都被这句话漂白。
吃是笼罩天穹的巨伞。甚至从生命还没有诞生,我们就开始吃了。构成我们肌体原初的那些物质:骨的钙,血的铁,瞳孔的胡萝卜素,头发的维生素原B5,肌肉的纤维,脑神经的沟回……无一不是我们从大自然攫取来的。生命始自吃大自然,大自然是胚胎化缘的钵,这就是最洪荒的缘分啊!
出生后,我们开始吃母亲。乳汁是世界上最完整最宜于消化吸收的养料。妈妈的胸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谷仓,遮风雨的帐篷,温暖的火墙和日夜轰响的交响乐团(资料证明,婴儿在母亲的心跳声中,感觉最安宁。因为这声音的节奏,已融入孩子永恒的记忆)。因为吃与被吃,母与子,结成天下无与伦比的友谊。这种友谊被庄严地称为——母爱。
长大了,我们开始吃自己。养活你自己,几乎是进入成人界最显著的标志。填平空虚的胃,曾经是多少人惨淡经营的梦想。待统计到国计民生上,温饱解决了,我们就能进入小康,吃——此刻不仅仅是食物,更成了逾越文明纪录的标杆。吃是基础,吃是栋梁。有了吃,一个民族才能在世界的麦克风中有扩大的声音。没有吃,肚子咕咕叫的动静压倒一切,遑论其它!
夫妻走到一块,叫做从此在一个饭锅里搅马勺了。吃是男女长久的媒人和粘合剂。
普天之下,熙熙攘攘,多少酒肆饭楼,早茶晚宴,都是为吃聚在一处。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大事在杯觥交错中议定,有多少金钱在餐桌下滚滚作声。
为了吃,人是残忍的,远古时曾尝遍了包括人自身在内的所有生物。进步了,不再吃人。科学了,不再吃有害健康的食物,但人的好吃仍是无与伦比。毒蛇有毒,拔了牙吃。河豚性烈,剥了内脏继续吃。珍禽异兽,都曾被人烹炸清炖,吃了南极吃北极,先是磷虾后是鲸……人是地球上能吃善吃的冠军,狮子老虎都得自叹弗如。
吃到遥远的地方,吃出奇异的境界,是人类永不磨灭的理想。所以人总想吃出地球去,吃到太空去,到另外的星球上找饭辙,这便是无限神往的明天了。
到什么也不想吃的时候,生命已到尾声,与这世界的缘分将尽了。所以能吃是最基本的缘分,切不可小觑。与“能吃”的可爱相比,功名利禄都是泔水。吃亦有道,需吃得聪明,吃得正大,吃得坦荡。吃的是自己双手挣来的清白,吃才是人间的幸福。
珍惜能吃的日子,珍惜一道举筷的亲人。珍惜畅饮的朋友,珍惜吃的智慧。敬畏热爱供给我们吃的原料,吃的场所,吃的机会,吃的概率的源头——大自然与母亲!
生命的借记卡
我有一个西式钱包,钱包里有很多小格子,这些格子的用途是装载各式各样的卡。我没让它们闲着,装的满满当当。我有附近多家超市的亲情卡,虽然我每次购物之后都毕恭毕敬地出示该店的卡,但一年下来累计的分数,总也到不了可以领取优惠券的地步(因为我购物不够专一,总是在各个不同的店家游荡)。于是就在某一个商家规定的日子里被残忍地“归零”,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我还有电话卡,到外地出差的时候,虽然接待方会很热情地说,房间的长途已经开通,您只管用。我还是为饭店附加在电话上的费用斤斤计较,出于为邀请方省些银两的考虑,自己到酒店大堂去打公用电话。每打一次,都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我还有几家馆子的优惠卡,有一次拿出来结账,服务员小姐看了半天,说不认识这卡,从来没见客人使过。我说,你来这家店多久了呢?她说,一年了。我说,这卡是你们店开张的时候给的,说是永久有效呢。小姐就拿了卡去问元老,笑吟吟地回来说,你说的不错,只是连她们也没见过这种卡,一直找到老板才说确有这么回事。
啰嗦了这半天,还没说到正题上。我的正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虽然有多张看起来也是硬邦邦闪烁烁的卡,但其实那种可以透支可以境外使用的货真价实的银行卡,一张也没有。先生说过很多次了,说这是时尚,你在高档场所结账的时候,如果掏出一大把皱皱巴巴的现金,是要遭人耻笑的。我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平日最频繁的交易场所就是农贸市场,别说那里没有刷卡的设备,即便有了,买上一个西瓜刷一次卡,买三条黄瓜斤半草莓再刷两次卡,你觉得如何呢?
于是家人就嘲讽我近乎一个纯粹的农妇,不能在金融方面与时俱进。好在这羞惭近日得到了雪洗的机会。单位为了发放工资方便,为大家统一办理了银行借记卡。
我拿到借记卡,反复端详并仔细地阅读了有关条文,突然思绪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
喜欢这个“借”字。我们的一切都是借来的,总归有要还的那一天。《红楼梦》里的公子贾宝玉出生的时候,嘴里是衔了一块玉的。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并非是两手空空,而是捏了一本生命的借记卡。
阳世通行的银行卡分有钻石卡白金卡等等细则,生命的卡则一律平等,并不因了出身的高下和财富的多寡,就对持卡人厚此薄彼。
这张卡是风做的,是空气做的,透明、无形,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拂动着我们的羽毛。
在你的亲人还没有为你写下名字的时候,这张卡就已经毫不迟延地启动了业务。卡上存进.了我们生命的总长度,它被分解成一分钟一分钟的时间,树木倾斜的阴影就是它轻轻的脚印了。
密码虽然在你的手里,但储藏在生命借记卡的这个数字,你虽是主人,却无从知道。这是一个永恒的秘密,不到借记卡归零的时候,你在混沌中。也许,它很短暂呢,幸好我不知你不知,咱们才能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懵然向前,支出着我们的时间,在哪一个早上那卡突然就不翼而飞,生命戛然停歇。
很多银行卡是可以透支的,甚至把透支当成一种福祉和诱饵,引领着我们超前消费,然而它也温柔地收取了不菲利息的。生命银行冷峻而傲慢,它可不搞这些花样,制度森严铁面无私。你存在账面上的数字,只会一天天一刻刻地义无反顾地减少,而绝不会增多。也许将来随着医学的进步,能把两张卡拼成一张卡,现阶段绝无可能,以后也要看生命银行的脸色,如果它太觉尊严被冒犯和亵渎,只怕也难以操作。咱们今天就不再讨论。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发布的生命预期表,人的寿命已经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想起来,很是令人神往呢。如果把这些年头折算成分分秒秒,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一小时3600秒……按照我们能活80年计算,卡上的时间共计是2522880000秒。(没找到计算器,老眼昏花地用笔算,反复演算了几遍,应该是准确的。)
真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下子呼吸也畅快起来,腰杆子也挺起来,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时间的大富翁。小过,且慢。既然算账,就要考虑周全。借记卡有一个名为“缴费通”的业务,可以代缴代扣。比如手机话费、小灵通话费、宽带上网费、水电费、图文电视费……呵呵,弹指间,你的必要消费就统统交付了。
生命也是有必要消费的。就在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卡上的数字就要减掉若干秒了。我们有很多必不可少的支出,你必须要优先保证。首先,令人晦气的是——我们要把借记卡上大约三分之一的数额,支付给床板。床板是个哑巴,从来不会对你大叫大喊,可它索要最急,日日不息。你当然可以欠着床板的账,它假装敦厚,不动声色。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八年,它不威逼你,是个温柔的黄世仁。它的阴险在长久的沉默之后渐渐显露,它不动声色地无声无息地报复你,让你面色干枯发摇齿动,烦躁不安歇斯底里……它会让你乖乖地把欠着它的钱加倍偿还,如果它不满意,还会把还账的你拒之门外。倘若你欠它的太多了,一怒之下,也许它会彻底撕毁了你的借记卡,纷纷扬扬飘失一地,让杨白劳就此永远躺下。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从长远计,你切不可以慢待了床板这个索债鬼,不管它多么笑容可掬,你每天都要按时还它时间。
你还要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吃饭、排泄、运动、交通、打电话,接吻、示爱和做爱,到远方去旅游,听朋友讲过去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发脾气和生气,和上司吵架还有哭泣……当然你也可以将这些压缩到更少的时间,但你如果在这些方面太吝啬支出的话,你就变成了一架冰冷的机器,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为了让我们的生命丰富多彩,这些支出你无法逃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