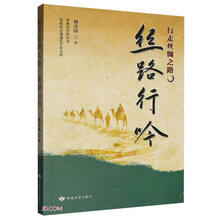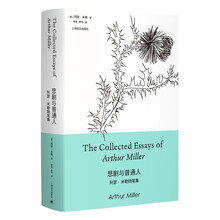帆船的一般驾驶是不难学的,而且是在风平浪静的湖面上,没有什么危险,很快大家就轮流掌舵。风力强劲的时候,严兹偶尔会给大家露一两手“高难动作”,把船驶得倾斜成45°角,船上的儿个人就叽哩哇啦一阵乱叫,迅速找好位置和角度,小心不要让自己掉到水里去。每当这个时候,大胖子文迪总可以找到H{武之地,站出来解大家的围,坐到适当的一侧,恢复船的平衡。他的体重大概有一百多公斤,是我们船上的大秤砣。如果夜里大家都躺在船舱里,或是早上还没起床时,他卜下船就会把船摇得像八九级地震一样,震波还久久不散。
海漠娜是个勤快的女孩。每天早上我们船出航前,她总是带着我把帆船的里里外外冲洗得干干净净。只是干净不了一会儿,男士们上船了,大鞋子噼噼啪啪地又会踩得一塌糊涂。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另一条船上的德国教练吉瑞不喜欢我。两条船一靠岸,他就开始跟在我身后不停地唠叨。他总能挑出我的错,什么我去买东西回来太晚让大家等啦,什么我不该在湖中心跳下去游泳啦……我不知道这个身材和睑蛋都漂亮得像个模特似的大男孩居然可以像个老太太似地那么婆婆妈妈。唠叨得我不而寸烦了,我就回过头来狠狠地跟他吵了两架。“我买东西回来晚了让你们大家等,是你们大家去逛大街回来晚了,先让我等的。既然我可以等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等我?”我知道我的水性只有1.70米深,就是说水真没过了我,我是不敢说我会游泳的。吉瑞为此事发脾气,其实是为我好。只是在那么多人面前下不了台的时候我也会强词夺理:“我是穿着救生衣跳下去的,能出什么事。”水性很好的大胖子文迪在旁边不慌不忙地举起了手,“出不了事,有我呢。”
吵过两次以后,吉瑞跟我,倒格外和睦了,凑在一起轻声细语地聊天。我在德国住了八九年,还是不懂德国人。
吉瑞的手很漂亮,细致、修长,格外秀气,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艺术气质。每次我看到他用手在船上船下拉纤绳的时候,心里总是替这双手可惜,它们更应该去弹钢琴的。后来吉瑞告诉我,他并不是职业教练,也不是这个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他在一家银行里工作,只是在夏天假期的时候,才到波兰来义务地为旅行社服务。
该哈德想出一个游戏。他端来浅浅的一盘水,一边各放一支草签,让文迪和F各占一边,先把草签吹到对岸的为胜。18岁的F和38岁的文迪便趴在地上,认真地鼓起腮邦子屏足了气,该哈德一声令下,他们使足了气力,只是吹了对方一脸水,草签早已不知去向——这个游戏是根本不会分出胜负的,结果就是让对手相互吹一脸的水。他们认真而滑稽的样子,让我们笑痛了肚子。
基尔夫妻中的那位先生,有一次不知何故要搬到我们船上来住一晚。本来是我和海漠娜各占一床,该哈德和文迪两位男士挤在船头的,他来住在我床上,我和海漠娜挤在一起。这位先生是很健谈的,经常是夜已近半,大家已经哈欠连天了,还听到他在高谈阔论着德国的政局以及内幕。让我觉得好笑的是德国的政治何必和这些人跑到波兰来谈,他老兄完全可以在基尔当地找个小酒馆坐进去,话题、场所和听众都合适得多。这位先生住到我们船上的这晚他没有谈政治,他三言两语地开着玩笑,我们另外四个笑着,笑声还没落,却听到他已起了鼾声。开始我们还以为他是故作幽默,叫了他几声,没应,果真已经睡着了。为此又让我们笑了好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