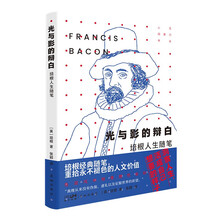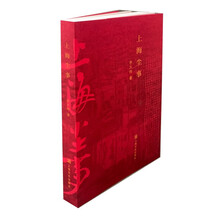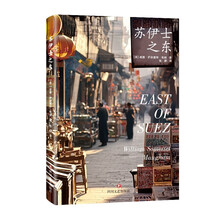在是否使用“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主要是一些老辈或老派学者)很反感“白银时代”的提法,认为它并不构成一个“时代”,他们很留恋前苏联学者那个明确却累赘的概念:“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似乎一用“白银时代”的概念,就是抬举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就是让它与其前辉煌的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其后繁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平起平坐了。其实,将前苏联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如索科洛夫等)的研究成果与当今有关“白银时代”的著作做一个比较,发现它们在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再者,“白银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与其前、其后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不能因为其持续的时间短而忽视其独具的内涵和外延。因此,“白银时代”不构成一个时代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再看一看实际情况:在欧美斯拉夫学术界,早在六十年代就启用了“白银时代”的概念,大学里一直开设有以此为题的课程,以其为内容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俄国,这一概念也已经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了,就是以前那些用惯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之概念的学者也转而采用更简洁、更顺口的“白银时代”了;而在我们这里,“白银时代”的说法即便不能说深入人心,至少也已让圈内人士耳熟能详了。所以,现在来谈论是否该使用“白银时代”的提法,似乎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但是,在目前关于“白银时代”这一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上,有两种倾向是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内涵宽泛化,另一种倾向是将“白银时代”的性质意识形态化。
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通常是指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和苏维埃文化之前这一时间段中的文化,它横亘在两个世纪的交接处,时间跨度为二十余年。关于“白银时代”的分期,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它大致的起止点还是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界定,即托尔斯泰之后和十月革命之前。当然,你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列耶夫等人的创作就已经显现出了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不同的一些特征;当然,你还可以说,十月革命并未能截然阻断“白银时代”的文化惯性。任何一个时代都与其前后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一个时期的划分因而也都是相对的。相比较而言,“白银时代”的划分倒还有着更为牢靠的依据,因为,作为其开端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有着与传统俄国文学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艺术趣味,而注重个人价值和艺术创新的“白银时代”文化,必然会在倡导集体和集权的十月政治革命后不久迅速地中止。面对这样一个相对清晰的文学史分期,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仍想做某种“扩大化”的工作,在尽量拉长、抻宽“白银时代”。有人欲加大“白银时代”的规模,认为其上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下限为斯大林时期的开始:有人则欲增加“白银时代”的内容,认为它不仅应该包括当时已近尾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新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而且还应该包括进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学说。在已经出版的一套关于“白银时代”的“丛书”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无疑已是“苏维埃时期”的作品,“丛书”中的另一部小说属于批判现实主义晚期,真正意义上的“白银时代”作品也许只有一部。我们认为,应该赋予“白银时代文化”以一个相对稳定、相对明确的界定,否则,失去了其内在规定性的“白银时代”概念,便会面临外延泛化的危险,乃至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再一种倾向,便是在对“白银时代”的理解上添加了很多的意识形态意味。上述一些人士对“白银时代”概念的反感,其中就包含有这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白银时代”的一些作家后来大多不接受十月革命,在革命后流亡国外,与后来的苏联文学一直处于对立状态,因而是不应大加宣传的。令人奇怪的是,有些鼓吹“白银时代”文化的学者却也持有与此相同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白银时代”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革命时与现实的距离和革命后与专制的对峙。这里,在低估或高估“白银时代”的人士身上都出现了一个“时代倒错”现象,即忽略了“白银时代”是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完全依赖其与之后时代的联系或在之后时代中的命运来看待它,是难以对它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的。于是,我们听到了关于“白银时代”文化为“颓废”文化的指责,我们听到了关于那一时期的作家“世界观落后”、“脱离人民”的说法。于是,我们更常在关于“白银时代”文字中读到某些作家的“悲剧”命运以及关于这些命运的感慨。有意无意之间,人们在将“白银时代”的文学等同于苏维埃时期的“境外流亡文学”、“非官方文学”乃至“持不同政见者文学”。例如,人们最近在谈论“白银时代”文学时,就时常提及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和叶甫图申科作品在内的花城版的《流亡者文丛》。有人还将索尔仁尼琴等人、甚至布罗茨基也归入了“白银时代”作家的行列。这一切都在强化“白银时代”文化与苏维埃文化的对立,并欲在这种对立中分出一个高低来。文化与专制,知识分子在集权统治下的命运,这只是“白银时代”文化的一个内容,不是其全部,而且还只是一个后来附加上去的内容。再者,对于文化与专制,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在谈到曼德里施塔姆的遭遇时,似乎是阿赫马托娃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换一种社会制度,曼德里施塔姆的命运也不一定就会好到哪里去。最近出版的一本索尔仁尼琴传记(《索尔仁尼琴传》,汤姆斯著,马丁出版社)写道,流亡到美国之后的索尔仁尼琴,与“金钱专制”下的美国社会同样是格格不入的,该传记的作者因而称索尔仁尼琴为“永恒的持不同政见者”。可见,纠缠在文化与专制之冲突这一点上,并将这一点视为“白银时代”文化之“重点”,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总之,给“白银时代”的文化添加过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既妨碍我们客观、冷静地评判其价值和意义,也不利于我们养成历史地接受文化遗产的良好习惯。
……
展开